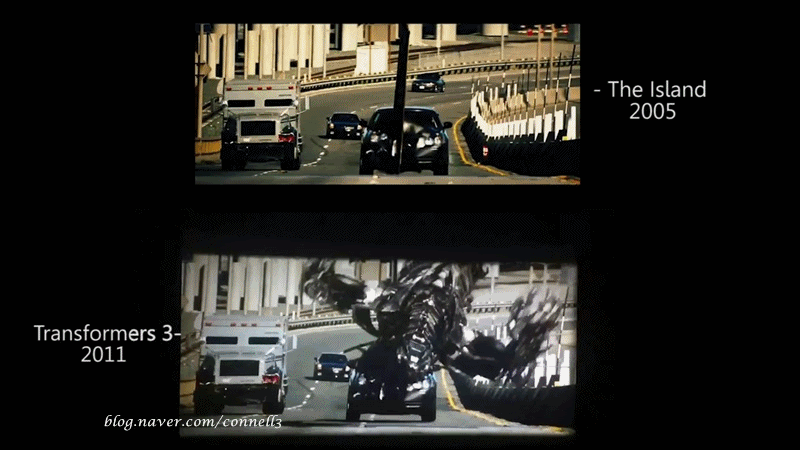京滬高鐵開通,舉國雀躍。
溫家寶說,京滬高鐵對於完善現代交通運輸體系、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滿足民眾出行需求意義重大,譜寫了中國鐵路建設史上的新篇章;
外國一些媒體對此浩大建設深表欣羨,暗嘆獨裁政權高效率之餘,亦說高鐵將
給中國帶來巨變云云。
另一邊廂,信報去週才報導,高鐵上座率低、虧損嚴重已不是什麼秘密,已運營的京津、武廣、鄭西、滬寧、滬杭五線幾無例外。事實上,全球唯一賺錢的高鐵線只有連接日本東京和大阪的
東海道新幹線,高鐵差不多與虧蝕畫上等號。看來,世上真的沒有免費午餐,要「完善現代交通運輸體系」,要「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要「滿足民眾出行需求」(全是溫總的話),要付代價的,代價就是高鐵的虧蝕,至少賺錢之前的虧蝕,如果終有一天賺錢的話。
高鐵為什麼這樣不濟?這不是本文有限篇幅及我這位門外漢能夠完滿回答的問題,我只能從興趣所及的幾方面探討一下。
往還二地,通常不只一種交通工具,我們的選擇建基於多項因素,如方便、準時、舒適、天氣、身體狀況,但最基本的考慮莫過於「成本 vs 快慢」;快些到達,不介意付貴一點;慢,當然得壓價了。成本和快慢,永遠是取捨,只可擇一。
平時說「成本」,指的是車資,這是消費者的角度。從工程師的角度,交通工具的「成本」可有另一番解讀。跑得快,風阻大,克服風阻要消耗能量,對工程師來說,風阻是一項成本,是交通工具運作時的必要付出。風阻以外,任何「阻力」都是成本,每種交通工具的總體「阻力成本」視乎其設計,「阻力成本」小,便能以最小能量最快移動最多貨物。1950 年,兩位工程師 G. Gabrielli 及 T. von Kármán 提出一條方程式,某交通工具的馬力除以重量再除以速度,就是其「阻力成本」,數值愈小愈好。注意,「阻力成本」是個物理數值,表示能量運用的效率,與金錢上的營運成本沒有必然關係。

2005 年,Imperial College London 機械工程系運用上述方程式,算出現今多種交通工具的阻力成本,繪成圖表。原圖頗為繁複,經我簡化成右圖。縱軸為阻力成本,橫軸為速度,每種運輸都能以不同速度前進,故形成五條軌跡;該圖顯示了「成本 vs 快慢」的取捨,速度愈快,阻力成本傾向愈高,不是絕對,大概如是。
若論最節省能源,非海運與鐵路莫屬。飛機雖然耗能,但勝在夠快,故仍有立足之地。車輛不算快,阻力成本又高(非常耗能),看似一無是處,為什麼還會存在?因其彈性及方便,其他運輸去不到的地方它都去得到。圖中「鐵路(客運)」那條軌跡涵蓋了時速 200 至 500 公里(留意橫軸為對數),包括了高鐵,以此圖看,高鐵在物理上一點不輸蝕,雖然不及飛機快,但阻力成本較低,應驗了「成本 vs 快慢」的取捨;與汽車比較更是「高下立見」,高鐵又快,阻力成本又低,物理上真看不到駕車的理由。
在物理層面,高鐵是不錯的運輸模式;其虧蝕連年,罪不在物理,答案要從其他方面找。
報導說,高鐵上座率低,貧苦大眾付不起高昂的車資云云。究竟,高鐵車費合理嗎?由北京去上海,傳統火車走 14 小時,收約 180 元(人民幣,下同);飛機兩小時多,機票千多元;高鐵兩者之間,車費怎樣才算合理?
首先,要把所有價格放到同一基礎上比較。有人採用每公里車資(車資除以距離),例如列車甲每公里 1 元,列車乙每公里 1.1 元,甲比乙便宜;但從消費者角度,這比較無甚實質意義,一公里究竟有多長?乘搭交通工具是用金錢換時間,時間才有切身意義,我愛用每分鐘車資。每分鐘車資愈高,每分鐘走的路應該愈遠(車速愈快),以下是四種北京至上海交通工具的計算:
- T109 號火車,每分鐘付 0.216 元走 1286 米。
- D33 號 250 公里時速高鐵,每分鐘付 0.775 元走 2010 米。
- G1 號 300 公里時速高鐵,每分鐘付 1.927 元走 3692 米。
- 某空中航班,每分鐘付 8.7 元飛 8290 米。
(注意,我計算速度是用二地的「直線距離」,並非路線長度,消費者只在乎向目的地進發,不理會途中的迂迴。)用同一手法,可比較來往任何二地、任何交通工具的價錢,我總共計算了京滬高鐵、武廣高鐵、京津高鐵、滬寧高鐵、滬杭高鐵、北京至上海的火車、武漢至廣州的火車、北京首都機場至上海虹橋機場的航班及武漢天河機場至廣州白雲機場的航班,繪出下圖。

原本打算分折高鐵票價,怎知圖畫了出來,更似分析航空公司劈價原因。如圖所示,若把二小時登機時間計算在內,飛機比高鐵快不了多少,但機票明顯貴了一截,如不劈價,根本無法競爭,還未計航班誤點、受天氣影響等不確定因素。圖中的劈價,是低於三折的劈價,頗為極端,航空公司能否經常提供,頗有疑問。看高鐵及火車票價,大致處於一條直線之上,單看此圖,高鐵不算過份昂貴,反而全費機票才是貴得嚇人。
既然票價不算高,為什麼高鐵少人問津?我真的沒有答案,只能懷疑中國老百姓未夠富有。早前經濟學人
一位論者說過,日本東海道新幹線賺錢的唯一原因是「the sheer density—and affluence—of the customers they serve」,一是人夠多,二是夠富裕。中國沿海省份的人口密度絕不比東海道新幹線遜色,可是財富遠遠不及。假如這位論者的說法正確,假以時日,中國某些高鐵線賺錢的可能性不容抹煞。
最後提出一個觀點,要求高鐵賺錢是否有點不公平?一間高鐵公司需要獨力承擔路軌及車廂二者的維修,反觀一間巴士公司,只需保養車輛,不必維修馬路;一間輪船公司,只需保養輪船,不必修揖水道;一間航空公司,只需保養飛機,不必保養航道。高鐵與其他運輸系統最不同之處是那條「專用軌道」,那條需要刻意修揖、又無法分擔成本的專用軌道。政府花在修揖馬路的費用,我們不會說它「蝕」掉納稅人的錢,因為這是「完善現代交通運輸體系、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滿足民眾出行需求」的必要之舉,同樣道理,維修路軌的費用應否視為政府促進社稷的必然開支?把高鐵和其他運輸系統看齊,維修路軌的支出應否撇除,不計入損益表之內?
假如高鐵真的能夠提高人民福祉,為什麼不降價至滿座,讓最多人享受高鐵的好處?票貴少人搭,蝕錢;票平多人搭,可能一樣蝕錢。一個「以民為本」的政府,怎揀?
(2011 年 7 月 7 日 信報副刊,以後逢週四刊登)

 回港後,地產商把經過告訴智囊。智囊眉頭一皺:「看來你要轉軚了。」「什麼?」「甲是你的朋友,但乙的贏面較高。」「我不明白,甲乙不是機會均等嗎?」「表面上係,不過……好難解釋,不如我跟你玩個遊戲。」智囊掏出三張撲克牌,攤在桌上:「三張牌之中,有一張係葵扇A,你估邊張?」地產商指一指左邊,智囊一聲不響,翻開中間那一張,說:「你看見了,中間這一張不是葵扇A,現在剩下左、右兩張牌,你原本揀左邊,現在我問你,轉唔轉軚揀右邊?」「唔轉,照揀左邊。」答案揭曉,葵扇A在右,地產商沒有抓緊轉軚機會,怨不得人。
回港後,地產商把經過告訴智囊。智囊眉頭一皺:「看來你要轉軚了。」「什麼?」「甲是你的朋友,但乙的贏面較高。」「我不明白,甲乙不是機會均等嗎?」「表面上係,不過……好難解釋,不如我跟你玩個遊戲。」智囊掏出三張撲克牌,攤在桌上:「三張牌之中,有一張係葵扇A,你估邊張?」地產商指一指左邊,智囊一聲不響,翻開中間那一張,說:「你看見了,中間這一張不是葵扇A,現在剩下左、右兩張牌,你原本揀左邊,現在我問你,轉唔轉軚揀右邊?」「唔轉,照揀左邊。」答案揭曉,葵扇A在右,地產商沒有抓緊轉軚機會,怨不得人。













 2005 年,Imperial College London 機械工程系運用上述方程式,算出現今多種交通工具的阻力成本,繪成圖表。原圖頗為繁複,經我簡化成右圖。縱軸為阻力成本,橫軸為速度,每種運輸都能以不同速度前進,故形成五條軌跡;該圖顯示了「成本 vs 快慢」的取捨,速度愈快,阻力成本傾向愈高,不是絕對,大概如是。
2005 年,Imperial College London 機械工程系運用上述方程式,算出現今多種交通工具的阻力成本,繪成圖表。原圖頗為繁複,經我簡化成右圖。縱軸為阻力成本,橫軸為速度,每種運輸都能以不同速度前進,故形成五條軌跡;該圖顯示了「成本 vs 快慢」的取捨,速度愈快,阻力成本傾向愈高,不是絕對,大概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