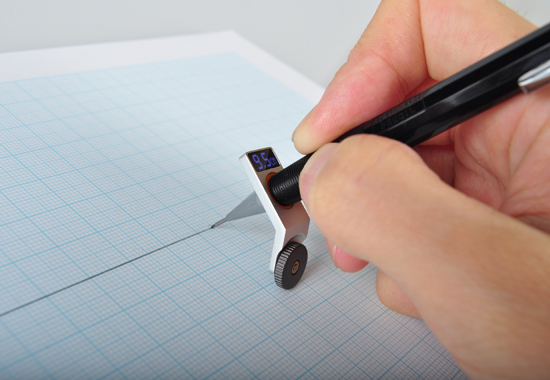設想,某天街上,一位陌生男子向你問路,正在指點方向之際,兩位不懂禮讓的裝修工人抬着一扇大木門在你倆中間穿過,視線被擋,你唯有待他們經過之後,再繼續指路。陌生人道謝,並說:「其實這是一個心理學實驗,剛才趁你視線被擋,問路人給調換了,我其實不是原先向你問路的人。」
你一定會問:「有冇可能呀?咁都唔發覺?」事實上,97% 的人認為自己一定察覺,餘下 3% 為何妄自菲薄,我不知道。
然而,正式實驗結果,54% 的人沒有察覺。眼前人「掉包」也有過半人毫不為意,簡直匪夷所思。
視而不見,心理學稱為「change blindness」,意指眼前影象有變,但我們見不到有變。大家有沒有發覺我今天換了名字?(按:刊文當日我改名為 Bruce Lee,翌日改回 Nick Lee 了。)
有的話,恭喜你。沒有的話,不必自卑,change blindness 十分常見,視野內的事物縱有轉變,不留意便未必察覺,這是人之常情。我人微言輕,看不見我的名字可以原諒,但是正在交談的人調換了也懵然不知,簡直就是「當人無到」!那次實驗飾演陌生人的兩位都是二十出頭的男性,身穿不同衣服,身高相差五厘米,聲線可辨,換句話說,他們不是孖生兒,但亦未至「判若兩人」。實驗同時發現,與陌生人年紀相約的途人,較易察覺「掉包」,人類本能顯然是較為留意「同類」。實驗再把演員裝扮成建築工人,果然減低被拆穿的機會(即使途人年齡相約)。
心理學家就是喜歡挑戰我們的「眼界」,揭示我們的「盲點」。我心想,他們一定知道,若兩位陌生人太不相像,例如一男一女、一老一嫩、或一光頭一 punk 頭,被拆穿的機會必會增加,兩人必須夠相像(盲點才會出現),但又不能太相像(否則盲點也沒有意義了)。不過話說回頭,是否一男一女便容易拆穿呢?真是未試過未知,畢竟多數人都高估了自己的辨別能力。
另一個實驗裡,電視畫面顯示三位穿白衫和三位穿黑衫的人把一個籃球傳來傳去,有些空中傳球,有些彈地傳球,有人拍球,你的任務是用心數着白隊或黑隊的傳球次數,整個片段 75 秒。看完後,研究員叫你寫下心中的數字,然後問:「剛才你在數數的時候,片段中可有特別事情發生?」四成的人說沒有。
其實在片段四十多秒處,一隻大猩猩從畫面左向右走,穿過傳球的人群。這不是一隻真的大猩猩,只是有人穿起大猩猩的戲服。你能想像竟然有四成人沒有看見嗎?又是 change blindness。
四成只是平均數,實驗其實測試了四種情況,受試者數其中一項:(一)白隊的傳球總次數;(二)黑隊的傳球總次數;(三)白隊的彈地和空中傳球次數;(四)黑隊的彈地和空中傳球次數。前二者明顯較容易,所需專注較少,故察覺大猩猩的機率高於後二者;此外,大猩猩與黑隊同色,注意黑隊的人亦較容易察覺大猩猩的存在。
Change blindness 的實驗,證實我們的感官不如想像中敏銳和清晰。驚訝之餘,不禁要問,可有改善之法?不幸地,學者對其外在因素雖有研究,但這畢竟牽涉人的本能,不是說一說便改得來,真要改的話,對身邊一草一木、一言一語、一字一標點都不放過,多加留意,謹小慎微便可,理論上不難,但實行起來是如何的費勁,如何的浪費精力?換個角度看,我們之所以「盲」,是腦袋自動過濾訊息,減少不必要負荷的結果。正常情況下,問路的陌生人不會無故「掉包」,籃球員中間不會有隻大猩猩(特別是要集中精神數着傳球次數的時候),腦袋自動替我們過濾「不必要」的訊息,就是要騰出腦力,給我們作「重要」的事。
可以這樣說,對於眼前一些轉變,我們雖然「盲」,但是「盲」得有道理,而且無傷大雅。接下來介紹另一種「盲」,後果可大可小,更加耐人尋味。
設想,你和研究員隔着桌子對坐,他拿出兩張女士相片(證件相大小,只顯示面部),問你哪位比較吸引?你指指其中一張,研究員把相片往桌面蓋下,推給你,你拿起相片後,研究員問:「為何選擇她呢?」不同人面對不同相片,當然有不同的答案。
有何特別?事實上,研究員玩了一個魔術,推給你的相片是另外一張,不是你選的那張。奇怪的是,超過三分二的人沒有發覺相片被換,心理學家稱此為「choice blindness」-- 自己選了什麼,自己也不清楚,比 change blindness「盲」得更嚴重。更奇怪的是,當問及相中女士有何吸引,多數人竟然說得出「原因」!這些「不經意」的回應,心理學稱為「confabulation」,直譯是「閒談」,我認為「齋噏」更貼切 -- 噏得就噏,說了便算。
怪事不止於此。實驗有兩部分,第一部分如上所述,玩魔術「整蠱」人,得來的回應全是「齋噏」;另一部分是誠實的,選那張給那張,沒施掩眼法,得來的回應應該是「可信」的。學者認為兩批回應必定有些潛在差異,對其作了潛在語義分析(latent semantic analysis),怎知它們竟然如出一轍!換言之,「齋噏」與「可信」,表面上沒有分別。
一天,我往陪父飲茶,在報攤買了《信報》,這是父親唯一愛讀的報紙。吃叉燒包之際,猛然發覺報攤給了一份《成報》,但見父親若無其事,捧着報紙讀得津津有味,我問:「點解你咁鍾意睇《信報》嘅?」他慢條斯理答道:「你鍾意點解,咪點解囉。」
(2010 年 8 月 31 日 信報副刊)
學術參考:
Petter Johansson, Lars Hall, Sverker Sikstrom, Betty Tarning, Andreas Lind (2006), “How Something Can Be Said about Telling More Than We Can Know: On Choice Blindness and Introspection,”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15, 673-692.
Petter Johansson, Lars Hall, Sverker Sikstrom, Andreas Olsson (2005), “Failure to Detect Mismatches Between Intention and Outcome in a Simple Decision Task,” Science 310, 116-119.
Daniel T. Levin, Nausheen Momen, Sarah B. Drivdahl (2000), “Change Blindness Blindness: The Metacognitive Error of Overestimating Change-detection Ability,” Visual Cognition 7, 397-412.
Daniel J. Simons, Christopher F. Chabris (1999), “Gorillas in Our Midst: Sustained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for Dynamic Events,” Perception 28, 1059-1074.
Daniel J. Simons, Daniel T. Levin (1998), “Failure to Detect Changes to People During a Real-World Interaction,”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5, 4, 644-649.
2010年8月31日 星期二
2010年8月29日 星期日
2010年8月24日 星期二
失憶情人
「Jason 和 Vincent 昨日竟然同時送花給我,你說我應該怎揀?」Connie 說。
「……你問我?」
她沒回答,呆望着我頭頂上的空氣。
「不如這樣,1 至 10 分,1 分『籮底橙』,10 分『lur 飯應』,Jason 你給多少分?」
她想了片刻,「7 分。」
「Vincent 呢?」
她想了想,皺一皺眉,「當然與 Jason 同分啦,否則我也不用煩惱。」
我沒回應,繼續吸吮杯中的溶冰。
幾個月後,她揀了 Jason。
某天晚上,我與 Connie 通電話,「今晚 Jason 沒接你放工嗎?」
「他去了英國工幹,下星期回來。」
「其實你喜歡 Jason 些什麼?」
「他……人好,又懂得逗我歡喜……這還不夠嗎?」接收不清,或是語帶猶豫,我不清楚。
「1 至 10 分,你會給他多少分?」
「……你說……什麼……」訊號忽然模糊起來,最終斷了線。
當晚,我們沒再通話,雖然不知道 Jason 得分,但我心裡有數。
曾有過這樣一個心理實驗,一位家庭主婦面對八件家庭電器,研究員叫她給電器評分,然後抽出兩件同分的供她選擇,她只能二擇其一帶回家,就像 Connie 必須在 Jason 和 Vincent 之間選擇一樣。家庭主婦作出選擇之後,研究員再叫她給八件電器評分,有趣的情形就在這時出現,原來同分的兩件,現在不再同分,選中那件得分提高,落選那件得分降低,家庭主婦彷彿要替自己的選擇「辯護」,以分數來「證明」已作選擇之正確。心理學家認為,先前的喜好與後來的行為不一致,形成一種「認知矛盾」(cognitive dissonance),要消除矛盾,已作的選擇既不能改,便只有改變內心喜惡,遂有把分數「舞高弄低」的現象。Jason 得分多少,我不知道,但肯定比從前的高。
翌日上班,得悉 Connie 昨晚發生車禍,我急急趕往醫院。踏入病房,看見 Vincent 床邊守候,心想,難道 Vincent 仍未死心?
「醫生說她腦部受了震盪,一些近期記憶可能受創,不過另無大礙,要留院觀察幾天。」Vincent 解釋。
「我對昨晚車禍毫無印象,不過幸好還認得所有來探望的人。」Connie 說着,帶點倦態。
待 Vincent 離開後,我問:「有沒有通知 Jason?」
她面露迷惘,「還未,為何要急着通知他?」
難道她忘了與 Jason 的關係?「其實……關於 Jason,你記得什麼?」
「記得他和 Vincent 同一天送花給我,我還問你應該怎揀。現在我不明白的是,既然 Vincent 都知道我入院,Jason 應該都收到消息,他遲遲不來探望,是否欠了一點誠意?」
「他去了英國工幹,原定下星期回來,我可以幫你通知,若你想讓他知道的話。」
她呆望着房間的牆角,心有所思。
Vincent 算不算「冷手執個熱煎堆」呢?Connie 的心,有否向一方傾斜?我再次在心理學文獻尋找答案。根據「認知矛盾」理論,Connie 對所作選擇毫無印象,心中沒有「矛盾」可言,故她對兩位男士的觀感應該「回到從前」,Vincent 可以「從頭開始」之餘,在 Jason 回來之前還有近水樓台的優勢。然而,近期研究開始質疑認知矛盾論,以下心理實驗便是一例。過程與上面家庭主婦挑選家用電器差不多,不過這次是失憶症病人挑選油畫,挑選前和挑選後分別對油畫評分;此「失憶症」不同 Connie 的失憶,它是一種持續的病態,因腦袋某部分受到永久傷害或腦袋缺乏維他命 B1 所致,病人舊記憶猶存,但不能製造新的記憶。換句話說,病人挑選了油畫之後,很快便會忘記,根據認知矛盾論,他們應該對所作選擇不存任何「情意結」,油畫評分理應前後一致。
研究結果出人意表,曾被選中的油畫第二次得分依然提高,落選的第二次得分依然下降,儘管評分的人忘記作過任何選擇。這是對傳統想法一記當頭棒喝,一向認為喜好(preference)決定行為(behaviour 或 decision),現在行為反過來支配喜好,不需清醒記得起,全是潛意識作祟。市場研究和經濟學這些專門研究或操縱人類行為的學科,又有新的課題了。
Connie 沉默良久,沒有回應。我走出房間,致電 Jason。未知 Connie 最終揀誰,但至少應該給予兩人公平的「起點」吧。
抑或,這次「重賽」根本沒有公平的可能,Connie 雖然忘記了和 Jason 一起的日子,但是一張寫過字的白紙,又怎能擦得一乾二淨?
(2010 年 8 月 24 日 信報副刊)
學術參考:
Géraldine Coppin, Sylvain Delplanque, Isabelle Cayeux, Christelle Porcherot, David Sander (2010), “I'm No Longer Torn After Choice: How Explicit Choices Implicitly Shape Preferences of Odor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 4, 489-493.
Louisa C. Egan, Laurie R. Santos, Paul Bloom (2007), “The Origins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Evidence from Children and Monkey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1, 978-983.
Matthew D. Lieberman, Kevin N. Ochsner, Daniel T. Gilbert, Daniel L. Schacter (2001), “Do Amnesics Exhibit Cognitive Dissonance Reduction? The Role of Explicit Memory and Attention in Attitude Change,” Psychological Science 12, 2, 135-140.
「……你問我?」
她沒回答,呆望着我頭頂上的空氣。
「不如這樣,1 至 10 分,1 分『籮底橙』,10 分『lur 飯應』,Jason 你給多少分?」
她想了片刻,「7 分。」
「Vincent 呢?」
她想了想,皺一皺眉,「當然與 Jason 同分啦,否則我也不用煩惱。」
我沒回應,繼續吸吮杯中的溶冰。
幾個月後,她揀了 Jason。
某天晚上,我與 Connie 通電話,「今晚 Jason 沒接你放工嗎?」
「他去了英國工幹,下星期回來。」
「其實你喜歡 Jason 些什麼?」
「他……人好,又懂得逗我歡喜……這還不夠嗎?」接收不清,或是語帶猶豫,我不清楚。
「1 至 10 分,你會給他多少分?」
「……你說……什麼……」訊號忽然模糊起來,最終斷了線。
當晚,我們沒再通話,雖然不知道 Jason 得分,但我心裡有數。
曾有過這樣一個心理實驗,一位家庭主婦面對八件家庭電器,研究員叫她給電器評分,然後抽出兩件同分的供她選擇,她只能二擇其一帶回家,就像 Connie 必須在 Jason 和 Vincent 之間選擇一樣。家庭主婦作出選擇之後,研究員再叫她給八件電器評分,有趣的情形就在這時出現,原來同分的兩件,現在不再同分,選中那件得分提高,落選那件得分降低,家庭主婦彷彿要替自己的選擇「辯護」,以分數來「證明」已作選擇之正確。心理學家認為,先前的喜好與後來的行為不一致,形成一種「認知矛盾」(cognitive dissonance),要消除矛盾,已作的選擇既不能改,便只有改變內心喜惡,遂有把分數「舞高弄低」的現象。Jason 得分多少,我不知道,但肯定比從前的高。
翌日上班,得悉 Connie 昨晚發生車禍,我急急趕往醫院。踏入病房,看見 Vincent 床邊守候,心想,難道 Vincent 仍未死心?
「醫生說她腦部受了震盪,一些近期記憶可能受創,不過另無大礙,要留院觀察幾天。」Vincent 解釋。
「我對昨晚車禍毫無印象,不過幸好還認得所有來探望的人。」Connie 說着,帶點倦態。
待 Vincent 離開後,我問:「有沒有通知 Jason?」
她面露迷惘,「還未,為何要急着通知他?」
難道她忘了與 Jason 的關係?「其實……關於 Jason,你記得什麼?」
「記得他和 Vincent 同一天送花給我,我還問你應該怎揀。現在我不明白的是,既然 Vincent 都知道我入院,Jason 應該都收到消息,他遲遲不來探望,是否欠了一點誠意?」
「他去了英國工幹,原定下星期回來,我可以幫你通知,若你想讓他知道的話。」
她呆望着房間的牆角,心有所思。
Vincent 算不算「冷手執個熱煎堆」呢?Connie 的心,有否向一方傾斜?我再次在心理學文獻尋找答案。根據「認知矛盾」理論,Connie 對所作選擇毫無印象,心中沒有「矛盾」可言,故她對兩位男士的觀感應該「回到從前」,Vincent 可以「從頭開始」之餘,在 Jason 回來之前還有近水樓台的優勢。然而,近期研究開始質疑認知矛盾論,以下心理實驗便是一例。過程與上面家庭主婦挑選家用電器差不多,不過這次是失憶症病人挑選油畫,挑選前和挑選後分別對油畫評分;此「失憶症」不同 Connie 的失憶,它是一種持續的病態,因腦袋某部分受到永久傷害或腦袋缺乏維他命 B1 所致,病人舊記憶猶存,但不能製造新的記憶。換句話說,病人挑選了油畫之後,很快便會忘記,根據認知矛盾論,他們應該對所作選擇不存任何「情意結」,油畫評分理應前後一致。
研究結果出人意表,曾被選中的油畫第二次得分依然提高,落選的第二次得分依然下降,儘管評分的人忘記作過任何選擇。這是對傳統想法一記當頭棒喝,一向認為喜好(preference)決定行為(behaviour 或 decision),現在行為反過來支配喜好,不需清醒記得起,全是潛意識作祟。市場研究和經濟學這些專門研究或操縱人類行為的學科,又有新的課題了。
Connie 沉默良久,沒有回應。我走出房間,致電 Jason。未知 Connie 最終揀誰,但至少應該給予兩人公平的「起點」吧。
抑或,這次「重賽」根本沒有公平的可能,Connie 雖然忘記了和 Jason 一起的日子,但是一張寫過字的白紙,又怎能擦得一乾二淨?
(2010 年 8 月 24 日 信報副刊)
學術參考:
Géraldine Coppin, Sylvain Delplanque, Isabelle Cayeux, Christelle Porcherot, David Sander (2010), “I'm No Longer Torn After Choice: How Explicit Choices Implicitly Shape Preferences of Odor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 4, 489-493.
Louisa C. Egan, Laurie R. Santos, Paul Bloom (2007), “The Origins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Evidence from Children and Monkey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1, 978-983.
Matthew D. Lieberman, Kevin N. Ochsner, Daniel T. Gilbert, Daniel L. Schacter (2001), “Do Amnesics Exhibit Cognitive Dissonance Reduction? The Role of Explicit Memory and Attention in Attitude Change,” Psychological Science 12, 2, 135-140.
tags:
信報,
psychology
2010年8月22日 星期日
「R」如何計?
關於上星期的文章,有人問我「R」如何計。
沒錯,根據生命表繪畫的存活曲線並不圓滑,其下的面積其實是一個個梯形,我就是靠這些梯形面積的總和來計算「R」。最後那個三角形,只要用簡單幾何計出「50 歲人口之十分一」與存活曲線的交點便可。匿名讀者,希望答到你的問題吧。

沒錯,根據生命表繪畫的存活曲線並不圓滑,其下的面積其實是一個個梯形,我就是靠這些梯形面積的總和來計算「R」。最後那個三角形,只要用簡單幾何計出「50 歲人口之十分一」與存活曲線的交點便可。匿名讀者,希望答到你的問題吧。

2010年8月17日 星期二
香港人,睇你點死
某地居民死得很特別,一半 60 歲壽終正寢,另一半 80 歲入土為安,整體平均壽命剛好 70 歲。若干年後,醫療改善,平均壽命提升至 75 歲,政府大悅,急急開記者招待會發佈喜訊,會上有記者問:「平均五歲的延長,究竟是原來 80 歲死的現在 90 歲才死,或是原來 60 歲死的現在 70 歲才死,或是兩者之間?」官員啞口無言。
一個平均數,隱藏往往比揭示的多,正如人均 GDP 無法反映貧富懸殊。根據世界銀行,本港男性平均壽命由 1971 年 67.80 歲增至 2008 年 79.33 歲,女性同期則由 75.30 歲增至 85.50 歲,延長的壽命來自老者愈老,還是(相對)早死的人少了?實情該是兩者之間,但哪個因素較為重要呢?
這是一個人口統計學練習,首要認識人口統計的最基本工具:存活曲線(survival curve)。

它告訴你活得超過某歲數的機會,上圖是發達地區的典型曲線,死亡多在五、六十歲之後,亦由於這個原因,我們只着眼於 50 歲後的曲線,始於圖中長方形的左上角。沿着曲線走,經過最陡斜的七、八十歲路段,來到長方形右下角,這是 50 歲人口的十分一。長方形可以採用不同的起點(左上角)和終點(右下角),例如以 40 歲為起點、40 歲人口的 5% 為終點亦無不可,視乎研究員的喜好或習慣。我採用 50 歲為起點、50 歲人口的十分一為終點,是跟隨早前兩位瑞士學者的做法,他們利用這個「moving rectangle」的概念拆解平均壽命上升「動力」何來。
看看長方形怎樣變化。假設老者愈老,但其他年齡存活率不變,長方形右下角便會向右拉,曲線以下面積(即圖中「R」部分)稍稍加大,但佔長方形的比例減小。另一個情況,假設老者不能再老,但(相對)早死的人多活幾年,則長方形寬度不變,但曲線更為陡斜,有如「後浪掩至」,「R」面積佔長方形的比例增加。由此可見,長方形變寬是「老者愈老」的標誌,「R」對長方形面積比是「後來追上」的指標,前者拉,後者推,延長平均壽命可說由這兩項「動力」構成。
兩位瑞士學者研究其祖國 1876-2006 年的人口資料,發現瑞士人的平均壽命增長,「老者愈老」和「後來追上」的貢獻各佔一半。這不是高深數學,只要有資料,我也能夠替香港算一算。政府統計處網頁載有 1971 年及後的香港人口生命表(life table),我根據其繪出 1971、1990 及 2009 年的存活曲線如下:
再計算 1971-1990 年及 1990-2009 年、兩項動力對壽命增長的貢獻:
注意,這方法只能捕捉長方形內的變化,儘管涵蓋大部分死亡人口,卻並非全部,故以上壽命增長不及香港整體。從表可見,「老者愈老」的貢獻大過「後來追上」,女性尤為明顯,前者佔壽命增長份額超過三分二,後者亦有貢獻,只是不及前者。
做完練習,看過長方形內曲線演變,長方形以外,亦有兩點值得留意。2009 年香港生命表顯示,100 位女性之中,9 人活至百歲以上,現時生命表依然沿用舊例,百歲以上沒有細分年齡,只以「100+」蔽之,看來統計處應該與時並進了,以一個「+」號統攬差不多十分一人口,不太恰當。
女比男長壽,眾所周知,由 0 歲開始女性已經較為「命硬」,至 100 歲皆如此,女士存活率「由頭帶到落尾」,這是香港 1971 年以來的常態(或許也是其他地區的常態,但不敢肯定)。可是,近來出現一個有趣現象,2007-2009 連續三年,男孩存活率竟比女孩高,20 歲左右女孩才「反超前」,回復常態。這個反常現象在上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從未出現過,後來隨着男女孩存活率差距收窄,九十年代偶有發生,但多屬曇花一現,歸咎或然率亦屬合理。2007-2009 接連在 20 歲以下「長期反常」,是不是有更深層的啟示?現代醫藥是否無意中偏重男孩呢?反常會否向更高年齡進發?其他地區有沒有相同現象?若這情況持續下去,人口學者和醫療專家便有新的課題了。
(2010 年 8 月 17 日 信報副刊)
補充:為了更清晰明瞭 2007-2009 年如何「反常」,先讓我們看看存活曲線於孩童時期的常態,以下是典型存活曲線的左端,女性自出娘胎存活率便高於男性:

出生後(0-1 歲)屬高危期,儘管情況比從前好。
上世紀九十年代,男孩存活率高於女孩的反常情況開始出現,但是一年即止,分別是 1991、1994 及 1999 年:
千禧年後,2004 年再現反常,然後 2007-2009 連續三年:
是否長期現象,多看幾年便知。
學術參考:
Valentin Rousson, Fred Paccaud (2010), “A Set of Indicators for Decomposing the Secular Increase of Life Expectancy,” Population Health Metrics 8, 18.
Siu Lan Karen Cheung, Jean-Marie Robine, Edward Jow-Ching Tu (2005),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Survival Curve: Horizontalization, Verticalization, and Longevity Extension,” Demography 42, 2, 243-258.
John R. Wilmoth, Shiro Horiuchi (1999), “Rectangularization Revisited: Variability of Age at Death within Human Populations,” Demography 36, 4, 475-495.
一個平均數,隱藏往往比揭示的多,正如人均 GDP 無法反映貧富懸殊。根據世界銀行,本港男性平均壽命由 1971 年 67.80 歲增至 2008 年 79.33 歲,女性同期則由 75.30 歲增至 85.50 歲,延長的壽命來自老者愈老,還是(相對)早死的人少了?實情該是兩者之間,但哪個因素較為重要呢?
這是一個人口統計學練習,首要認識人口統計的最基本工具:存活曲線(survival curve)。

它告訴你活得超過某歲數的機會,上圖是發達地區的典型曲線,死亡多在五、六十歲之後,亦由於這個原因,我們只着眼於 50 歲後的曲線,始於圖中長方形的左上角。沿着曲線走,經過最陡斜的七、八十歲路段,來到長方形右下角,這是 50 歲人口的十分一。長方形可以採用不同的起點(左上角)和終點(右下角),例如以 40 歲為起點、40 歲人口的 5% 為終點亦無不可,視乎研究員的喜好或習慣。我採用 50 歲為起點、50 歲人口的十分一為終點,是跟隨早前兩位瑞士學者的做法,他們利用這個「moving rectangle」的概念拆解平均壽命上升「動力」何來。
看看長方形怎樣變化。假設老者愈老,但其他年齡存活率不變,長方形右下角便會向右拉,曲線以下面積(即圖中「R」部分)稍稍加大,但佔長方形的比例減小。另一個情況,假設老者不能再老,但(相對)早死的人多活幾年,則長方形寬度不變,但曲線更為陡斜,有如「後浪掩至」,「R」面積佔長方形的比例增加。由此可見,長方形變寬是「老者愈老」的標誌,「R」對長方形面積比是「後來追上」的指標,前者拉,後者推,延長平均壽命可說由這兩項「動力」構成。
兩位瑞士學者研究其祖國 1876-2006 年的人口資料,發現瑞士人的平均壽命增長,「老者愈老」和「後來追上」的貢獻各佔一半。這不是高深數學,只要有資料,我也能夠替香港算一算。政府統計處網頁載有 1971 年及後的香港人口生命表(life table),我根據其繪出 1971、1990 及 2009 年的存活曲線如下:
再計算 1971-1990 年及 1990-2009 年、兩項動力對壽命增長的貢獻:
| 「老者愈老」 貢獻年歲 | 「後來追上」 貢獻年歲 | 長方形內 平均壽命總增長 | |
| 男,1971-1990 | 2.67 | 1.68 | 4.35 |
| 男,1990-2009 | 2.33 | 2.05 | 4.38 |
| 女,1971-1990 | 2.06 | 0.98 | 3.04 |
| 女,1990-2009 | 3.70 | 1.53 | 5.23 |
注意,這方法只能捕捉長方形內的變化,儘管涵蓋大部分死亡人口,卻並非全部,故以上壽命增長不及香港整體。從表可見,「老者愈老」的貢獻大過「後來追上」,女性尤為明顯,前者佔壽命增長份額超過三分二,後者亦有貢獻,只是不及前者。
做完練習,看過長方形內曲線演變,長方形以外,亦有兩點值得留意。2009 年香港生命表顯示,100 位女性之中,9 人活至百歲以上,現時生命表依然沿用舊例,百歲以上沒有細分年齡,只以「100+」蔽之,看來統計處應該與時並進了,以一個「+」號統攬差不多十分一人口,不太恰當。
女比男長壽,眾所周知,由 0 歲開始女性已經較為「命硬」,至 100 歲皆如此,女士存活率「由頭帶到落尾」,這是香港 1971 年以來的常態(或許也是其他地區的常態,但不敢肯定)。可是,近來出現一個有趣現象,2007-2009 連續三年,男孩存活率竟比女孩高,20 歲左右女孩才「反超前」,回復常態。這個反常現象在上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從未出現過,後來隨着男女孩存活率差距收窄,九十年代偶有發生,但多屬曇花一現,歸咎或然率亦屬合理。2007-2009 接連在 20 歲以下「長期反常」,是不是有更深層的啟示?現代醫藥是否無意中偏重男孩呢?反常會否向更高年齡進發?其他地區有沒有相同現象?若這情況持續下去,人口學者和醫療專家便有新的課題了。
(2010 年 8 月 17 日 信報副刊)
補充:為了更清晰明瞭 2007-2009 年如何「反常」,先讓我們看看存活曲線於孩童時期的常態,以下是典型存活曲線的左端,女性自出娘胎存活率便高於男性:

出生後(0-1 歲)屬高危期,儘管情況比從前好。
上世紀九十年代,男孩存活率高於女孩的反常情況開始出現,但是一年即止,分別是 1991、1994 及 1999 年:
千禧年後,2004 年再現反常,然後 2007-2009 連續三年:
是否長期現象,多看幾年便知。
學術參考:
Valentin Rousson, Fred Paccaud (2010), “A Set of Indicators for Decomposing the Secular Increase of Life Expectancy,” Population Health Metrics 8, 18.
Siu Lan Karen Cheung, Jean-Marie Robine, Edward Jow-Ching Tu (2005),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Survival Curve: Horizontalization, Verticalization, and Longevity Extension,” Demography 42, 2, 243-258.
John R. Wilmoth, Shiro Horiuchi (1999), “Rectangularization Revisited: Variability of Age at Death within Human Populations,” Demography 36, 4, 475-495.
tags:
信報,
health,
research-it-myself,
statistics
2010年8月11日 星期三
2010年8月10日 星期二
《交易現場》太陽黑子篇
太陽乃萬物之母,地球上的一切,由大氣層厚薄和海平面溫度至農作物收成,均與太陽的強弱有着微妙關係。觀察太陽黑子是窺探太陽的最直接途徑,黑子多寡與太陽強弱成正比,過去數年黑子數目偏低,太陽偏弱,地球接收的能量減少,對氣候影響如何?
去年 4 月,我發表了〈太陽黑子如股市〉一文,論及黑子數目雖然 11 年一個循環,但其短期走勢深不可測,科學家屢試屢敗。
太陽黑子和地球氣候,要預測時有迹可尋,要準確預測卻近乎不可能,正是培養所謂「專家」的最佳土壤,某地《交易現場》節目某日請來某位太陽黑子專家分析市場去向,節錄如下。
主持:歡迎收看 8 月 4 日《交易現場》。我們原本邀請了一位太陽黑子專家來為大家分析各類與太陽活動有關的市場去向,不過可能由於今日會考放榜,交通極為擠塞,他要遲一點才到。我趁機替大家重溫一下近年黑子走勢。
最近這次黑子低潮,各位應該記憶猶新。2008 年黑子出現日數只有 101 日,創近百年新低,很多科學家認為見底,預測翌年將見反彈,怎知 2009 年首季太陽黑子更為稀疏,反彈之日遙遙無期。正當市場意興闌珊,同年 5 月黑子漸有起色,年底還大量湧現,最終 2009 年有 103 日見太陽黑子,比 2008 年多兩日。當時,很多黑子期貨投資者給太陽「玩殘」,08 年底押重注翌年反彈,09 年初的市況簡直令人膽戰心驚,若你當時止蝕,則只有「眼白白」看着後市回升。
今年反彈之勢持續,看來太陽黑子已經步入上升周期,至於後市點睇,便要問專家……大師慢慢行,呌順條氣先,萬料不到會考放榜竟然引致交通癱瘓。
專家:睇番今早塞車嘅情況嚟講,或許由於早前有「日冕物質噴發」(coronal mass ejection,簡稱 CME),大量帶電粒子朝地球衝來,可能影響車輛的電子儀器,所以司機駕車份外小心。
主持:這個「日…冕…物質噴發」究竟是什麼回事?電子儀器之外,還有什麼會受影響?
專家:睇番呢個日冕物質噴發,其實是一些物質從太陽表面浮起,形成一個巨型的電漿泡泡,爆破時把大量帶電粒子噴出。現在太陽黑子正值上升週期,太陽愈趨活躍,這類噴發應會愈來愈多。至於其他方面嘅影響嚟講,輸電網、人造衛星、電腦都可能會受干擾,基本上嚟講任何電器都可能會受影響。極端嘅情況嚟講,例如 1989 年加拿大魁北克省電網便曾遭癱瘓。另外,極光奇景(aurora)亦會較易見到。
主持:即是說,每有日冕噴發,我們都可以留意一下電力股、電器股、科技股、旅遊股、極光期貨等等,對嗎?
專家:睇番呢個日冕噴發嚟講,強度未必足以影響日常生活,而且太陽活動只是剛剛冒出低潮,離高位尚遠。據一些科學家估計嚟講,2013 年才是太陽黑子高峰期,那時受噴發影響的機會相對高些。
主持:那是否表示司機暫時也不用過慮呢?
專家:可以咁講。
主持:如果司機聽見大師的高見,道路應會暢通不少。話說回頭,會考生人數只得 12 萬,佔全港人口不到 2%,應該不會對交通造成這麼大的影響吧!
專家:其實作為塞車嘅因素嚟講,會考生人數雖少,卻未必不會引致塞車。舉例,太陽活動高峰和低潮之間,釋出的能量只有 0.1% 之差,但地面溫度會因而起伏 0.06 至 0.1 度,大氣層較高處起伏更明顯,海拔 6 公里有 0.3 度,20 公里有 0.9 度。氣候其他方面嚟講,世界各處的氣壓系統與太陽都有關連,高、低壓區的位置會隨黑子週期而改變,最近甚至有研究顯示,水都威尼斯的週期性氾濫亦是跟隨黑子週期,假若 2013 年黑子高峰期屬實,那年氾濫的機會將會增加。
太陽能量只有 0.1% 之差,與受影響天然現象之廣泛根本不成比例,很多科學家從前都抱懷疑態度,近年數據漸多,規律才見明顯。對於氣候和很多社會現象嚟講,因果未必成比例,大家睇唔通的話,還是安全至上。
主持:明白。又到基礎分析環節,我們知道哪些現象與太陽黑子掛鈎,但為何這樣呢?箇中原因,我們知道多少?
專家:睇番科學界現時嚟講,仍未有結論,其中一個說法是,太陽的磁場會幫地球阻隔宇宙射線,而宇宙射線又會影響雲的形成,雲又會反過來阻隔日光,減少地球接收的能量。換言之,太陽除了直接照射地球,還會通過其他途徑來間接支配氣候,理論多的是,但結論未曾有。對於研究氣候嚟講,其實難處十分多,又厄爾尼諾,又溫室效應,又北極震盪,地球只有一個,十萬件事同時發生,混亂過十萬個為什麼,很難分清孰因孰果。對於散戶嚟講,又是那一句,睇唔清便不要入市。
主持:大師見解果然獨到。節目結束之前,對太陽黑子長線點睇?
專家:長線嚟講,有兩點大家要留意。首先嚟講,早前有科學家指出,過去 70 年的太陽活動是異常的高,來年未必能夠持續,換言之,過去 70 年的數據未必是理想指標。其次,睇番 08、09 年,太陽黑子剛剛渡過百年一遇的低潮,今年反彈早是意料中事,問題是反彈至多高及持續多久。睇番歷史嚟講,太陽黑子曾經有過多次「漫長熊市」,分別是 1010-1090 年的奧爾特低潮(Oort Minimum)、1282-1342 年的沃爾夫低潮(Wolf Minimum)、1416-1534 年的史波勒低潮(Sporer Minimum)、1645-1715 年的蒙德低潮(Maunder Minimum)和 1790-1830 年的道爾頓低潮(Dalton Minimum),低潮之間多數相隔 75-100 年,最長 200 年,睇番上次道爾頓低潮於 1830 年結束,距今差不多 200 年了,一次漫長低潮將至,甚或已至,一點不出奇,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主持:今日時間又到,請問大師有冇持有任何黑子期貨?
專家:好明顯係冇嘅。
主持:多謝大師講解,午飯時段再見。
(2010 年 8 月 10 日 信報副刊)
學術參考:
David Barriopedro, Ricardo García‐Herrera, Piero Lionello, Cosimo Pino (2010), “A Discussion of the Links between Solar Variability and High-Storm-Surge Events in Venice,”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15, D13101.
David H. Hathaway, Robert M. Wilson (2004), “What the Sunspot Record Tells Us about Space Climate,” Solar Physics 224, 5-19.
S. K. Solanki, I. G. Usoskin, B. Kromer, M. Schussler, J. Beer (2004), “Unusual Activity of the Sun During Recent Decades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11,000 Years,” Nature 431, 1084-1087.
Judith Lean, David Rind (2001), “Earth's Response to a Variable Sun,” Science 292, 234-236.
D. Camuffo, C. Secco, P. Brimblecombe, J. Martin-Vide (2000), “Sea Storms in the Adriatic Sea and the Western Mediterranean During the Last Millennium,” Climate Change 46, 209-223.
P. Christoforou, S. Hameed (1997), “Solar Cycle and the Pacific 'Centers of Action',”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4, 3, 293-296.
Joanna D. Haigh (1996), “The Impact of Solar Variability on Climate,” Science 272, 981-984.
去年 4 月,我發表了〈太陽黑子如股市〉一文,論及黑子數目雖然 11 年一個循環,但其短期走勢深不可測,科學家屢試屢敗。
太陽黑子和地球氣候,要預測時有迹可尋,要準確預測卻近乎不可能,正是培養所謂「專家」的最佳土壤,某地《交易現場》節目某日請來某位太陽黑子專家分析市場去向,節錄如下。
***
主持:歡迎收看 8 月 4 日《交易現場》。我們原本邀請了一位太陽黑子專家來為大家分析各類與太陽活動有關的市場去向,不過可能由於今日會考放榜,交通極為擠塞,他要遲一點才到。我趁機替大家重溫一下近年黑子走勢。
最近這次黑子低潮,各位應該記憶猶新。2008 年黑子出現日數只有 101 日,創近百年新低,很多科學家認為見底,預測翌年將見反彈,怎知 2009 年首季太陽黑子更為稀疏,反彈之日遙遙無期。正當市場意興闌珊,同年 5 月黑子漸有起色,年底還大量湧現,最終 2009 年有 103 日見太陽黑子,比 2008 年多兩日。當時,很多黑子期貨投資者給太陽「玩殘」,08 年底押重注翌年反彈,09 年初的市況簡直令人膽戰心驚,若你當時止蝕,則只有「眼白白」看着後市回升。
今年反彈之勢持續,看來太陽黑子已經步入上升周期,至於後市點睇,便要問專家……大師慢慢行,呌順條氣先,萬料不到會考放榜竟然引致交通癱瘓。
專家:睇番今早塞車嘅情況嚟講,或許由於早前有「日冕物質噴發」(coronal mass ejection,簡稱 CME),大量帶電粒子朝地球衝來,可能影響車輛的電子儀器,所以司機駕車份外小心。
主持:這個「日…冕…物質噴發」究竟是什麼回事?電子儀器之外,還有什麼會受影響?
專家:睇番呢個日冕物質噴發,其實是一些物質從太陽表面浮起,形成一個巨型的電漿泡泡,爆破時把大量帶電粒子噴出。現在太陽黑子正值上升週期,太陽愈趨活躍,這類噴發應會愈來愈多。至於其他方面嘅影響嚟講,輸電網、人造衛星、電腦都可能會受干擾,基本上嚟講任何電器都可能會受影響。極端嘅情況嚟講,例如 1989 年加拿大魁北克省電網便曾遭癱瘓。另外,極光奇景(aurora)亦會較易見到。
主持:即是說,每有日冕噴發,我們都可以留意一下電力股、電器股、科技股、旅遊股、極光期貨等等,對嗎?
專家:睇番呢個日冕噴發嚟講,強度未必足以影響日常生活,而且太陽活動只是剛剛冒出低潮,離高位尚遠。據一些科學家估計嚟講,2013 年才是太陽黑子高峰期,那時受噴發影響的機會相對高些。
主持:那是否表示司機暫時也不用過慮呢?
專家:可以咁講。
主持:如果司機聽見大師的高見,道路應會暢通不少。話說回頭,會考生人數只得 12 萬,佔全港人口不到 2%,應該不會對交通造成這麼大的影響吧!
專家:其實作為塞車嘅因素嚟講,會考生人數雖少,卻未必不會引致塞車。舉例,太陽活動高峰和低潮之間,釋出的能量只有 0.1% 之差,但地面溫度會因而起伏 0.06 至 0.1 度,大氣層較高處起伏更明顯,海拔 6 公里有 0.3 度,20 公里有 0.9 度。氣候其他方面嚟講,世界各處的氣壓系統與太陽都有關連,高、低壓區的位置會隨黑子週期而改變,最近甚至有研究顯示,水都威尼斯的週期性氾濫亦是跟隨黑子週期,假若 2013 年黑子高峰期屬實,那年氾濫的機會將會增加。
太陽能量只有 0.1% 之差,與受影響天然現象之廣泛根本不成比例,很多科學家從前都抱懷疑態度,近年數據漸多,規律才見明顯。對於氣候和很多社會現象嚟講,因果未必成比例,大家睇唔通的話,還是安全至上。
主持:明白。又到基礎分析環節,我們知道哪些現象與太陽黑子掛鈎,但為何這樣呢?箇中原因,我們知道多少?
專家:睇番科學界現時嚟講,仍未有結論,其中一個說法是,太陽的磁場會幫地球阻隔宇宙射線,而宇宙射線又會影響雲的形成,雲又會反過來阻隔日光,減少地球接收的能量。換言之,太陽除了直接照射地球,還會通過其他途徑來間接支配氣候,理論多的是,但結論未曾有。對於研究氣候嚟講,其實難處十分多,又厄爾尼諾,又溫室效應,又北極震盪,地球只有一個,十萬件事同時發生,混亂過十萬個為什麼,很難分清孰因孰果。對於散戶嚟講,又是那一句,睇唔清便不要入市。
主持:大師見解果然獨到。節目結束之前,對太陽黑子長線點睇?
專家:長線嚟講,有兩點大家要留意。首先嚟講,早前有科學家指出,過去 70 年的太陽活動是異常的高,來年未必能夠持續,換言之,過去 70 年的數據未必是理想指標。其次,睇番 08、09 年,太陽黑子剛剛渡過百年一遇的低潮,今年反彈早是意料中事,問題是反彈至多高及持續多久。睇番歷史嚟講,太陽黑子曾經有過多次「漫長熊市」,分別是 1010-1090 年的奧爾特低潮(Oort Minimum)、1282-1342 年的沃爾夫低潮(Wolf Minimum)、1416-1534 年的史波勒低潮(Sporer Minimum)、1645-1715 年的蒙德低潮(Maunder Minimum)和 1790-1830 年的道爾頓低潮(Dalton Minimum),低潮之間多數相隔 75-100 年,最長 200 年,睇番上次道爾頓低潮於 1830 年結束,距今差不多 200 年了,一次漫長低潮將至,甚或已至,一點不出奇,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主持:今日時間又到,請問大師有冇持有任何黑子期貨?
專家:好明顯係冇嘅。
主持:多謝大師講解,午飯時段再見。
(2010 年 8 月 10 日 信報副刊)
學術參考:
David Barriopedro, Ricardo García‐Herrera, Piero Lionello, Cosimo Pino (2010), “A Discussion of the Links between Solar Variability and High-Storm-Surge Events in Venice,”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15, D13101.
David H. Hathaway, Robert M. Wilson (2004), “What the Sunspot Record Tells Us about Space Climate,” Solar Physics 224, 5-19.
S. K. Solanki, I. G. Usoskin, B. Kromer, M. Schussler, J. Beer (2004), “Unusual Activity of the Sun During Recent Decades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11,000 Years,” Nature 431, 1084-1087.
Judith Lean, David Rind (2001), “Earth's Response to a Variable Sun,” Science 292, 234-236.
D. Camuffo, C. Secco, P. Brimblecombe, J. Martin-Vide (2000), “Sea Storms in the Adriatic Sea and the Western Mediterranean During the Last Millennium,” Climate Change 46, 209-223.
P. Christoforou, S. Hameed (1997), “Solar Cycle and the Pacific 'Centers of Action',”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4, 3, 293-296.
Joanna D. Haigh (1996), “The Impact of Solar Variability on Climate,” Science 272, 981-984.
2010年8月4日 星期三
2010年8月3日 星期二
拔河新玩法
今天玩拔河:

不過,有三條特別規則:
(1)開始前,每人之間的繩段不得拉緊。
(2)握繩不得移位。
(3)站立位置不得移動。
你問,那豈不是只有第一人在拉?
未必,因為身體可作有限度的前後傾斜:

問題是,多少人後才拉不緊?這要視乎很多變數,包括兩人之間的繩段長度和前後傾斜的幅度。舉個極端的例子,每人相隔一米,但兩人之間有三十米長的繩,不用計算也知道只有第一人「孤軍作戰」;假若兩人之間繩長 1.0001 米,那可能「排隊排到尖沙咀」繩子依然繃緊。
你問,誰玩這樣無聊的遊戲?知道繩子繃緊至何處又有何用處?
用處起碼有二:一曰軍事,一曰蜘蛛絲。
假設我要派遣占士邦及他的複製人深入敵方陣地跟蘇聯間諜拔河,最好預先試探拔河規則,計算所需人手,恰到好處地把繩拉緊,既可爭取拔河佳績向國民交差,亦不用浪費人手站在寬鬆繩段,騰出占士邦做些間諜應該做的事。一句話,我需要有效調配人手,用最少占士邦做最多最有利我國的任務。
蜘蛛絲的處境跟我差不多,但它不是有效運用 James Bond,而是有效運用 hydrogen bond(氫鍵)。兩星期前,我談過把原子(atom)扣在一起的各種化學鍵(chemical bond),當中不包括氫鍵,因為氫鍵在分子(molecule)之間才起作用,吸引力遠比原子間的化學鍵為小。上星期,我談過蜘蛛絲的強度媲美鋼,其韌度更超過任何人造物料,令科學家摸不着頭腦的是,蜘蛛絲由蛋白分子構成,其力量源自蛋白分子之間的氫鍵,但是氫鍵的力量微弱,蜘蛛絲怎樣利用氫鍵達致「超凡」的強韌?
蜘蛛絲包含兩種蛋白:一種條狀,像一堆散落一地的領帶;另一種塊狀,如領帶堆上貼上膠布。絲的強韌,取決於膠布和領帶之間的氫鍵排列。回到拔河比喻,參賽者就是氫鍵,拔河繩是條狀蛋白,地面是塊狀蛋白。蜘蛛絲被外力拉扯,拔河比賽便開始。那三項特別規例,實是物理現實的反映。塊狀和條狀蛋白之間,氫鍵只發生在特定位置,不能隨意滑動,是故參賽者手不得移位,腳不得移動。條狀蛋白並非直線,而是螺旋(像 DNA),會被外力拉直,故兩人之間的繩段開賽前不得拉緊。現在的問題是,塊狀和條狀蛋白之間最好有多少個氫鍵呢?太少,力量不足;太多,浪費資源;哪個數字最佳?
上面說過,最佳數字視乎各項變數,例如氫鍵之間條狀蛋白的長度、拆開氫鍵所需的能量等,最近有科學家發展出一套「拔河模型」,形容塊狀和條狀蛋白的氫鍵排列,輸入各項相關變數,算出三至四個氫鍵為最佳。換句話說,每條繩不宜多於四位拔河選手,若有十二位選手,分拉三條繩必定好過同拉一條。塊狀蛋白沒有拔河選手站於其上,它有的是相隔特定距離的氫鍵「據點」,無巧不成話,真實蜘蛛絲塊狀蛋白的長度大多能夠容納二至五個氫鍵,與「拔河模型」的預測不相伯仲,兩者有出入是自然的,一來天然生產的結構不可能毫無瑕疵,二來任何模型也無法完全反映現實,其預測與實況相約,已間接表明其可信性。這是科學界首次證明塊狀蛋白有一最適長度,而且蜘蛛絲的強弱與塊狀蛋白的大小有直接關係。
三至四個氫鍵為一組,這是蜘蛛絲的「魔術數字」。有了這個「魔術數字」,它便懂得最有效地運用手上資源,以最少物質發揮最大潛能。
(2010 年 8 月 3 日 信報副刊)
學術參考:
Sinan Keten, Markus J. Buehler (2010), “Nanostructure and Molecular Mechanics of Spider Dragline Silk Protein Assemblies,”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Interface, doi:10.1098/rsif.2010.0149
Sinan Keten, Zhiping Xu, Britni Ihle, Markus J. Buehler (2010), “Nanoconfinement Controls Stiffness, Strength and Mechanical Toughness of Beta -Sheet Crystals in Silk,” Nature Materials 9, 359-367.
Sinan Keten, Markus J. Buehler (2008), “Geometric Confinement Governs the Rupture Strength of H-bond Assemblies at a Critical Length Scale,” Nano Letters 8, 2, 743-748.
Sinan Keten, Markus J. Buehler (2008), “Asymptotic Strength Limit of Hydrogen-Bond Assemblies in Proteins at Vanishing Pulling Rates,”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00, 198301.
Sinan Keten, Markus J. Buehler (2008), “Strength Limit of Entropic Elasticity in Beta-Sheet Protein Domains,” Physical Review E 78, 061913.
A. A. Griffith (1921), “The Phenomena of Rupture and Flow in Solid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A 221, 163-198.

不過,有三條特別規則:
(1)開始前,每人之間的繩段不得拉緊。
(2)握繩不得移位。
(3)站立位置不得移動。
你問,那豈不是只有第一人在拉?
未必,因為身體可作有限度的前後傾斜:

問題是,多少人後才拉不緊?這要視乎很多變數,包括兩人之間的繩段長度和前後傾斜的幅度。舉個極端的例子,每人相隔一米,但兩人之間有三十米長的繩,不用計算也知道只有第一人「孤軍作戰」;假若兩人之間繩長 1.0001 米,那可能「排隊排到尖沙咀」繩子依然繃緊。
你問,誰玩這樣無聊的遊戲?知道繩子繃緊至何處又有何用處?
用處起碼有二:一曰軍事,一曰蜘蛛絲。
假設我要派遣占士邦及他的複製人深入敵方陣地跟蘇聯間諜拔河,最好預先試探拔河規則,計算所需人手,恰到好處地把繩拉緊,既可爭取拔河佳績向國民交差,亦不用浪費人手站在寬鬆繩段,騰出占士邦做些間諜應該做的事。一句話,我需要有效調配人手,用最少占士邦做最多最有利我國的任務。
蜘蛛絲的處境跟我差不多,但它不是有效運用 James Bond,而是有效運用 hydrogen bond(氫鍵)。兩星期前,我談過把原子(atom)扣在一起的各種化學鍵(chemical bond),當中不包括氫鍵,因為氫鍵在分子(molecule)之間才起作用,吸引力遠比原子間的化學鍵為小。上星期,我談過蜘蛛絲的強度媲美鋼,其韌度更超過任何人造物料,令科學家摸不着頭腦的是,蜘蛛絲由蛋白分子構成,其力量源自蛋白分子之間的氫鍵,但是氫鍵的力量微弱,蜘蛛絲怎樣利用氫鍵達致「超凡」的強韌?
蜘蛛絲包含兩種蛋白:一種條狀,像一堆散落一地的領帶;另一種塊狀,如領帶堆上貼上膠布。絲的強韌,取決於膠布和領帶之間的氫鍵排列。回到拔河比喻,參賽者就是氫鍵,拔河繩是條狀蛋白,地面是塊狀蛋白。蜘蛛絲被外力拉扯,拔河比賽便開始。那三項特別規例,實是物理現實的反映。塊狀和條狀蛋白之間,氫鍵只發生在特定位置,不能隨意滑動,是故參賽者手不得移位,腳不得移動。條狀蛋白並非直線,而是螺旋(像 DNA),會被外力拉直,故兩人之間的繩段開賽前不得拉緊。現在的問題是,塊狀和條狀蛋白之間最好有多少個氫鍵呢?太少,力量不足;太多,浪費資源;哪個數字最佳?
上面說過,最佳數字視乎各項變數,例如氫鍵之間條狀蛋白的長度、拆開氫鍵所需的能量等,最近有科學家發展出一套「拔河模型」,形容塊狀和條狀蛋白的氫鍵排列,輸入各項相關變數,算出三至四個氫鍵為最佳。換句話說,每條繩不宜多於四位拔河選手,若有十二位選手,分拉三條繩必定好過同拉一條。塊狀蛋白沒有拔河選手站於其上,它有的是相隔特定距離的氫鍵「據點」,無巧不成話,真實蜘蛛絲塊狀蛋白的長度大多能夠容納二至五個氫鍵,與「拔河模型」的預測不相伯仲,兩者有出入是自然的,一來天然生產的結構不可能毫無瑕疵,二來任何模型也無法完全反映現實,其預測與實況相約,已間接表明其可信性。這是科學界首次證明塊狀蛋白有一最適長度,而且蜘蛛絲的強弱與塊狀蛋白的大小有直接關係。
三至四個氫鍵為一組,這是蜘蛛絲的「魔術數字」。有了這個「魔術數字」,它便懂得最有效地運用手上資源,以最少物質發揮最大潛能。
(2010 年 8 月 3 日 信報副刊)
學術參考:
Sinan Keten, Markus J. Buehler (2010), “Nanostructure and Molecular Mechanics of Spider Dragline Silk Protein Assemblies,”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Interface, doi:10.1098/rsif.2010.0149
Sinan Keten, Zhiping Xu, Britni Ihle, Markus J. Buehler (2010), “Nanoconfinement Controls Stiffness, Strength and Mechanical Toughness of Beta -Sheet Crystals in Silk,” Nature Materials 9, 359-367.
Sinan Keten, Markus J. Buehler (2008), “Geometric Confinement Governs the Rupture Strength of H-bond Assemblies at a Critical Length Scale,” Nano Letters 8, 2, 743-748.
Sinan Keten, Markus J. Buehler (2008), “Asymptotic Strength Limit of Hydrogen-Bond Assemblies in Proteins at Vanishing Pulling Rates,”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00, 198301.
Sinan Keten, Markus J. Buehler (2008), “Strength Limit of Entropic Elasticity in Beta-Sheet Protein Domains,” Physical Review E 78, 061913.
A. A. Griffith (1921), “The Phenomena of Rupture and Flow in Solid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A 221, 163-198.
訂閱:
文章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