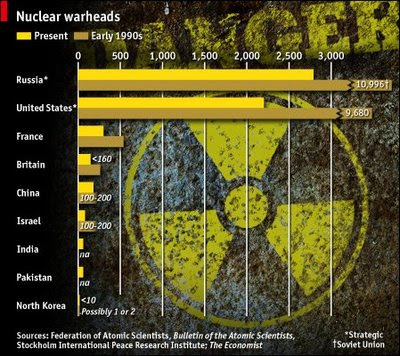剛發現了Synesthesia Battery,一個「標準化」的聯覺測試,讓科學家以劃一的標準去研究聯覺,看來頗有意思。如果你懷疑自己有聯覺,又或者你肯定自己是聯覺人,我鼓勵你到這個網站做做測試,說不定會遇到很多跟你相似的人。
計劃負責人David Eagleman最近還接受了Seed Magazine的一個訪問。
2009年5月27日 星期三
我愛中文(唔係因為我係中國人)
前文(到這裡,或轆落一篇)提到synaesthesia此字的由來。我根據這篇論文,Anomalous Perception in Synaesthesia: A Cognitive Neuroscience Perspective. Anina N. Rich, Jason B. Mattingley.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2002) volume 3, 43-52,而採用以下說法:
... from the Greek syn meaning 'union' and aisthises meaning 'of the senses' ...
細心的編輯問,aisthises可為aisthesis?的確,wikipedia說:
... from the Ancient Greek σύν (syn), "together," and αἴσθησις (aisthēsis), "sensation" ... (記住這個link,一陣有用)
真係考起,看來要到希臘一趟……我的假設是,其實兩者都o岩:
aisthises = of the senses
aisthēsis = sensation
但是,怎會加個of在前就連串法都不一樣?我用google translate,把英文翻譯成希臘文(我全部用眾數,減少變數):
of the senses = των αισθήσεων
sensations = αισθήσεις
最後兩個字母不同(暫時不要理會開頭那個三個字母)。
再到上面那個wiki的希臘文αἴσθησις網頁,頁內載有這個字的文法,其中一部份叫Inflection,重點在此。Inflection即是同一個字在不同情況下使用會有不同的串法,英文的sense,眾數是senses,過去式是sensed,都是inflection的例子,希臘文的inflection比英文複雜。
請點擊show字把列表伸展。對照字母,你會發現:
of the senses = των αισθήσεων(plural/Genitive)
sensations = αισθήσεις(plural/Nominative)
希臘文的noun有5個cases,nominative和genitive是其中兩個,什麼是cases,請看:
http://www.ntgreek.org/learn_nt_greek/nouns1.htm#CASES
在genitive case底下,說到:
... It is generally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with a prepositional phrase starting with the word "of" ...
換句話說,希臘文裡,of <a noun>是以這個noun的genitive case代表,看來google的釋法沒錯。至於怎樣從希臘字母轉成英文字母,我不得而知了。
對於希臘文而言,of something是會改變something的串法的。aisthesis或aisthises,應該只是有否of的分別。不過說到底,還是不肯定,因為不知道希臘串法怎樣轉成英文串法。看來,還是要去希臘一趟。 =)
從前一次寫英文文章,某字的inflection搞到我頭都大(又是一些模稜兩可的情況)。自此便發覺中文的「好處」,中文是世上極少數沒有inflection的文字。我愛中文,因為中文沒有麻煩的inflection。
... from the Greek syn meaning 'union' and aisthises meaning 'of the senses' ...
細心的編輯問,aisthises可為aisthesis?的確,wikipedia說:
... from the Ancient Greek σύν (syn), "together," and αἴσθησις (aisthēsis), "sensation" ... (記住這個link,一陣有用)
真係考起,看來要到希臘一趟……我的假設是,其實兩者都o岩:
aisthises = of the senses
aisthēsis = sensation
但是,怎會加個of在前就連串法都不一樣?我用google translate,把英文翻譯成希臘文(我全部用眾數,減少變數):
of the senses = των αισθήσεων
sensations = αισθήσεις
最後兩個字母不同(暫時不要理會開頭那個三個字母)。
再到上面那個wiki的希臘文αἴσθησις網頁,頁內載有這個字的文法,其中一部份叫Inflection,重點在此。Inflection即是同一個字在不同情況下使用會有不同的串法,英文的sense,眾數是senses,過去式是sensed,都是inflection的例子,希臘文的inflection比英文複雜。
請點擊show字把列表伸展。對照字母,你會發現:
of the senses = των αισθήσεων(plural/Genitive)
sensations = αισθήσεις(plural/Nominative)
希臘文的noun有5個cases,nominative和genitive是其中兩個,什麼是cases,請看:
http://www.ntgreek.org/learn_nt_greek/nouns1.htm#CASES
在genitive case底下,說到:
... It is generally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with a prepositional phrase starting with the word "of" ...
換句話說,希臘文裡,of <a noun>是以這個noun的genitive case代表,看來google的釋法沒錯。至於怎樣從希臘字母轉成英文字母,我不得而知了。
對於希臘文而言,of something是會改變something的串法的。aisthesis或aisthises,應該只是有否of的分別。不過說到底,還是不肯定,因為不知道希臘串法怎樣轉成英文串法。看來,還是要去希臘一趟。 =)
從前一次寫英文文章,某字的inflection搞到我頭都大(又是一些模稜兩可的情況)。自此便發覺中文的「好處」,中文是世上極少數沒有inflection的文字。我愛中文,因為中文沒有麻煩的inflection。
我看見A是紅色,B是綠色,你信嗎?
(刊於2009年5月27日信報副刊)
看題目,你可能認為我神經錯亂;其實,這是一種不算罕見的感官現象,叫「聯覺」,洋稱synaesthesia(美式串法synesthesia),是由希臘文的syn跟aisthises組成,前者意謂union,後者意謂of the senses,即兩種通常是分開的感官結合一起,例如5是黃色的,聽C音會嘗到酸味,吃甜感覺是圓的,甚至「信報」兩字勾起口中一陣鹹魚味亦無不可,組合繁多,讀者大可隨意想像。想像得到就有可能,卻不代表科學家曾經遇過。(信我,世上發生過的事,被記錄下來的只屬少數。)
聯覺的記載已有過百年歷史,其研究只是最近十多年方進入主流。過去,科學家對聯覺的普遍性存在很大分歧,有的估計四人之中有一個,也有估計十萬人才有一個。2006年,英國幾位研究聯覺的權威合力進行了史上最客觀的調查,估計聯覺人口比例為4.4%,並發現擁有聯覺的男女比例相約,打破了傳統上認為女多男少的謬誤(註[1])。換句話說,20-25人之中便有一位擁有聯覺,讀者中如有聯覺人,我不會感到奇怪;沒有,才是天大怪事。(如果你有聯覺,歡迎留言,只是好奇,得個知字。)
聯覺的種類,以「外來刺激→異常感覺」來劃分,如果你看見N是藍色,你便有「英文字母→顏色」的聯覺;吃甜感到很圓,是「味道→形狀」;信報勾起鹹魚味,就是「詞語→味道」,如此類推(一位聯覺人同時擁有數種聯覺並不罕見)。至今發現了超過50種聯覺,最常見的「異常感覺」是顏色,例如數字、英文字母、詞語、月份、周日(指一周七日)、音樂皆可勾起顏色。不過,我讀過的聯覺研究全在西方進行,尤其是英國和美國,當中一些概念未必能夠照搬來中國社會,例如中文沒有字母,只有數以萬計的字元;英文的月份和周日在串法和視覺上與日常數字完全無關,不像中文般把數字包含其中;這些文化差異,對聯覺的出現、分類和普遍性有何影響?本人未見有關研究。
科學家對聯覺的興趣,源於其可能揭示腦袋的運作。由於人道關係,科學家鮮有直接拿人腦做實驗,因此他們對一些「不正常」的人很有興趣,如自閉症、精神分裂症患者和聯覺人,希望找出其腦袋與常人的異同,籍此推敲「正常」腦袋的運作。(由此可見,正常不正常,是相對的,社會上的大多數永遠是「正常」的。)
告訴你,我也有聯覺:A是紅色,64也是紅色。你問:「這叫聯覺嗎?這是聯想。」你說得對,聯覺必須是不由自主,不經思維的。再告訴你,我真的有聯覺:我看見B是綠色,5是黃色的。你想:「沒有明顯的關連,不似是聯想。不過文人多大話,唔知信你定唔信你好……」你想得好,求真是科學研究必須的態度。科學家當然有一套驗証聯覺的方法,確保我不是在聯想,更不是在空談。
假設你是正常人,沒有聯覺。科學家在你面前出示一張紙牌,紙牌上印著一個有顏色的字母,你要盡快說出紙牌上字母的顏色。第一張是紅色的A,你肯定地說:「紅色。」第二張是黃色的B,你更加肯定地說:「黃色。」科學家說實驗完畢,你迷惑地離開,不知底蘊。輪到我這位自稱有聯覺的人,我告訴科學家:「我看見A是紅色,B是綠色,你信唔信?」科學家的回應,竟是向我出示一張「紅牌」,一張印有紅色A的牌,顏色跟我的聯覺吻合,因此我比你更加肯定更加敏捷地說:「紅色。」第二張牌,我看見一個B字,不禁眼前一「綠」,定神再看清楚,原來牌上的B是黃色的,我戰戰競競地說:「……黃黃黃……黃色……」科學家比你和我更加肯定地說:「我信。」(這是一位很馬虎的科學家,讀下去便明所以。)這就是心理學界(不單是聯覺)十分著名的Stroop effect,你說看見英文字母有顏色嗎,我就拿不同顏色的字母來擾亂你,有些跟你說的顏色吻合,有些不吻合,測試的重點,是量度吻合和不吻合時回答需時的「相差」。正常人沒有吻合不吻合之分,無論什麼字母什麼顏色,回答所需時間相約。有「英文字母→顏色」聯覺的人,回答不吻合顏色需時明顯較長。

(說明:圖的上部是聯覺者感到不同字母的顏色;左邊的字母跟聯覺吻合,右邊不吻合。受字母本身的顏色干擾,聯覺者需要較長時間才能讀出右邊字母的顏色。注意,這位聯覺者與我的聯覺不一樣,他的B是黃色,我的B是綠色。來源:Anomalous Perception in Synaesthesia: A Cognitive Neuroscience Perspective. Anina N. Rich, Jason B. Mattingley.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2002) volume 3, 43-52)
順帶一提,聯覺勾起的所謂「顏色」,在見者眼中可能以不同方式出現,因人而異,可以是重疊在字母之上,圍繞在字母周圍,也可以是一種純粹內在的感覺。可以肯定的是,顏色無論如何顯現,都不會完全蓋過字母本身的顏色,兩者只會同時存在。(註[2])
Stroop test可根據測試對象而變化。數年前,瑞士一位音樂家聲稱擁有「音程→味道」之聯覺(tone interval→taste),口中味道會根據聽見之音程而改變,例如小二度是酸,大三度是甜。(音程是兩個單音之間的「距離」;對鋼琴而言,音程亦即兩鍵之間的距離。)音樂的聯覺,通常是「單音→顏色」(tone→color)或「單音→形狀」(tone→shape);這是第一次「音程→味道」之記錄。驗証的方法,是讓這位音樂家耳聽音程的同時,在其舌頭加添味道,當之與聯覺不吻合,他嘗出味道所需的時間也相應加長。(註[3])
Stroop effect是驗証某感覺不由自主、不經思維的重要工具,這是聯覺的第一要求;可是,這未能滿足科學家的懷疑精神,他們對聯覺還有第二個要求:穩定,不因時間而改變。試想,如果我想冒充聯覺人,首次測試中假扮Stroop effect應有的遲緩反應而瞞天過海,數月後作第二次測試會怎樣?第一次要扮得「真實」殊不容易,幾個月後再重複幾個月前的「戲」,更難。不單要記得哪處反應慢,還要重複快慢反應的「時間差」,不是沒可能,但必須處心積慮。替我做實驗的那位科學家未經再試便說「我信」,與一位未想清楚便說「我願意」的新郎同樣魯莽。事實上,現代所有聯覺研究皆會在數周或數月後替參與者進行重複測試(有些甚至是突擊測試),以確保結果的真確。以下是一個較為極端的例子。
一位英國人,當他聽、講、讀某些詞語的時候,口中會嘗到一些十分具體而細膩的味道,不是普通的甜酸苦辣,而是諸如「浸過羅宋湯的麵包」、「塗了些少牛油的多士」、「又凍又硬的煙肉」和「易碎的餅乾」之類包括溫度和口感的形容(這是「詞語→味道」的聯覺,比較罕見,類似文首提過的「信報」勾起鹹魚味)。由於這些味道的多元化和複雜性,Stroop test並不管用,要驗証,只有憑其穩定性。首先,在這位聯覺人的幫助下,科學家收集了1195個日常詞語及其勾起的味道,可分為三類:沒有味道、有味道、有味道但不知怎樣形容的味道。四個月後,科學家選出88個屬於後二類的詞語再作訪問,聯覺人的回應與先前非常吻合。四年後,科學家再從那1195個詞語中隨意抽出50個作訪問,聯覺人全部答中。仍不滿意?對,負責研究的科學家仍未滿意。實情是,除了重複訪問之外,這兩次相隔四年的研究還做了不少額外且繁複的驗証(又是那六個字:篇幅所限,不贅);最後,科學家還是說了一句:「我信。」(註[4、5])
本文想帶給讀者的是,由於聯覺純是內在主觀的,以科學方法客觀驗証有其根本上的難度,對言者不能盡信的同時,聽者只能以間接方法窺其所思。任何牽涉主觀感覺的研究,與法庭定罪一樣,永遠沒有絕對肯定這回事,只有beyond reasonable doubt。聯覺是不由自主兼且穩定的異常感官,科學家為了証明其存在,創作各種巧妙的實驗,甚至耗費多年心血,這種求真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再次告訴你,我看見64是紅色的,你信唔信?
備註:
[1]Synaesthesia: The prevalence of atypical cross-modal experiences. Julia Simner, Catherine Mulvenna, Noam Sagiv, Elias Tsakanikos, Sarah A Witherby, Christine Fraser, Kirsten Scott, Jamie Ward. Perception (2006) volume 35, pages 1024-1033.
[2]Synaesthesia: An Overview of Contemporary Findings and Controversies. Jamie Ward and Jason B. Mattingley. Cortex (2006) volume 42, pages 129-136.
[3]When coloured sounds taste sweet. Gian Beeli, Michaela Esslen, Lutz Jäncke. Nature (2005) volume 434, page 38.
[4]Lexical-gustatory synaesthesia: linguistic and conceptual factors. Jamie Ward, Julia Simner. Cognition (2003) volume 89, pages 237–261.
[5]Synaesthetic Consistency Spans Decades in a Lexical–Gustatory Synaesthete. Julia Simner, Robert H. Logie. Neurocase (2007) volume 13, pages 358–365.
看題目,你可能認為我神經錯亂;其實,這是一種不算罕見的感官現象,叫「聯覺」,洋稱synaesthesia(美式串法synesthesia),是由希臘文的syn跟aisthises組成,前者意謂union,後者意謂of the senses,即兩種通常是分開的感官結合一起,例如5是黃色的,聽C音會嘗到酸味,吃甜感覺是圓的,甚至「信報」兩字勾起口中一陣鹹魚味亦無不可,組合繁多,讀者大可隨意想像。想像得到就有可能,卻不代表科學家曾經遇過。(信我,世上發生過的事,被記錄下來的只屬少數。)
聯覺的記載已有過百年歷史,其研究只是最近十多年方進入主流。過去,科學家對聯覺的普遍性存在很大分歧,有的估計四人之中有一個,也有估計十萬人才有一個。2006年,英國幾位研究聯覺的權威合力進行了史上最客觀的調查,估計聯覺人口比例為4.4%,並發現擁有聯覺的男女比例相約,打破了傳統上認為女多男少的謬誤(註[1])。換句話說,20-25人之中便有一位擁有聯覺,讀者中如有聯覺人,我不會感到奇怪;沒有,才是天大怪事。(如果你有聯覺,歡迎留言,只是好奇,得個知字。)
聯覺的種類,以「外來刺激→異常感覺」來劃分,如果你看見N是藍色,你便有「英文字母→顏色」的聯覺;吃甜感到很圓,是「味道→形狀」;信報勾起鹹魚味,就是「詞語→味道」,如此類推(一位聯覺人同時擁有數種聯覺並不罕見)。至今發現了超過50種聯覺,最常見的「異常感覺」是顏色,例如數字、英文字母、詞語、月份、周日(指一周七日)、音樂皆可勾起顏色。不過,我讀過的聯覺研究全在西方進行,尤其是英國和美國,當中一些概念未必能夠照搬來中國社會,例如中文沒有字母,只有數以萬計的字元;英文的月份和周日在串法和視覺上與日常數字完全無關,不像中文般把數字包含其中;這些文化差異,對聯覺的出現、分類和普遍性有何影響?本人未見有關研究。
科學家對聯覺的興趣,源於其可能揭示腦袋的運作。由於人道關係,科學家鮮有直接拿人腦做實驗,因此他們對一些「不正常」的人很有興趣,如自閉症、精神分裂症患者和聯覺人,希望找出其腦袋與常人的異同,籍此推敲「正常」腦袋的運作。(由此可見,正常不正常,是相對的,社會上的大多數永遠是「正常」的。)
告訴你,我也有聯覺:A是紅色,64也是紅色。你問:「這叫聯覺嗎?這是聯想。」你說得對,聯覺必須是不由自主,不經思維的。再告訴你,我真的有聯覺:我看見B是綠色,5是黃色的。你想:「沒有明顯的關連,不似是聯想。不過文人多大話,唔知信你定唔信你好……」你想得好,求真是科學研究必須的態度。科學家當然有一套驗証聯覺的方法,確保我不是在聯想,更不是在空談。
假設你是正常人,沒有聯覺。科學家在你面前出示一張紙牌,紙牌上印著一個有顏色的字母,你要盡快說出紙牌上字母的顏色。第一張是紅色的A,你肯定地說:「紅色。」第二張是黃色的B,你更加肯定地說:「黃色。」科學家說實驗完畢,你迷惑地離開,不知底蘊。輪到我這位自稱有聯覺的人,我告訴科學家:「我看見A是紅色,B是綠色,你信唔信?」科學家的回應,竟是向我出示一張「紅牌」,一張印有紅色A的牌,顏色跟我的聯覺吻合,因此我比你更加肯定更加敏捷地說:「紅色。」第二張牌,我看見一個B字,不禁眼前一「綠」,定神再看清楚,原來牌上的B是黃色的,我戰戰競競地說:「……黃黃黃……黃色……」科學家比你和我更加肯定地說:「我信。」(這是一位很馬虎的科學家,讀下去便明所以。)這就是心理學界(不單是聯覺)十分著名的Stroop effect,你說看見英文字母有顏色嗎,我就拿不同顏色的字母來擾亂你,有些跟你說的顏色吻合,有些不吻合,測試的重點,是量度吻合和不吻合時回答需時的「相差」。正常人沒有吻合不吻合之分,無論什麼字母什麼顏色,回答所需時間相約。有「英文字母→顏色」聯覺的人,回答不吻合顏色需時明顯較長。

(說明:圖的上部是聯覺者感到不同字母的顏色;左邊的字母跟聯覺吻合,右邊不吻合。受字母本身的顏色干擾,聯覺者需要較長時間才能讀出右邊字母的顏色。注意,這位聯覺者與我的聯覺不一樣,他的B是黃色,我的B是綠色。來源:Anomalous Perception in Synaesthesia: A Cognitive Neuroscience Perspective. Anina N. Rich, Jason B. Mattingley.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2002) volume 3, 43-52)
順帶一提,聯覺勾起的所謂「顏色」,在見者眼中可能以不同方式出現,因人而異,可以是重疊在字母之上,圍繞在字母周圍,也可以是一種純粹內在的感覺。可以肯定的是,顏色無論如何顯現,都不會完全蓋過字母本身的顏色,兩者只會同時存在。(註[2])
Stroop test可根據測試對象而變化。數年前,瑞士一位音樂家聲稱擁有「音程→味道」之聯覺(tone interval→taste),口中味道會根據聽見之音程而改變,例如小二度是酸,大三度是甜。(音程是兩個單音之間的「距離」;對鋼琴而言,音程亦即兩鍵之間的距離。)音樂的聯覺,通常是「單音→顏色」(tone→color)或「單音→形狀」(tone→shape);這是第一次「音程→味道」之記錄。驗証的方法,是讓這位音樂家耳聽音程的同時,在其舌頭加添味道,當之與聯覺不吻合,他嘗出味道所需的時間也相應加長。(註[3])
Stroop effect是驗証某感覺不由自主、不經思維的重要工具,這是聯覺的第一要求;可是,這未能滿足科學家的懷疑精神,他們對聯覺還有第二個要求:穩定,不因時間而改變。試想,如果我想冒充聯覺人,首次測試中假扮Stroop effect應有的遲緩反應而瞞天過海,數月後作第二次測試會怎樣?第一次要扮得「真實」殊不容易,幾個月後再重複幾個月前的「戲」,更難。不單要記得哪處反應慢,還要重複快慢反應的「時間差」,不是沒可能,但必須處心積慮。替我做實驗的那位科學家未經再試便說「我信」,與一位未想清楚便說「我願意」的新郎同樣魯莽。事實上,現代所有聯覺研究皆會在數周或數月後替參與者進行重複測試(有些甚至是突擊測試),以確保結果的真確。以下是一個較為極端的例子。
一位英國人,當他聽、講、讀某些詞語的時候,口中會嘗到一些十分具體而細膩的味道,不是普通的甜酸苦辣,而是諸如「浸過羅宋湯的麵包」、「塗了些少牛油的多士」、「又凍又硬的煙肉」和「易碎的餅乾」之類包括溫度和口感的形容(這是「詞語→味道」的聯覺,比較罕見,類似文首提過的「信報」勾起鹹魚味)。由於這些味道的多元化和複雜性,Stroop test並不管用,要驗証,只有憑其穩定性。首先,在這位聯覺人的幫助下,科學家收集了1195個日常詞語及其勾起的味道,可分為三類:沒有味道、有味道、有味道但不知怎樣形容的味道。四個月後,科學家選出88個屬於後二類的詞語再作訪問,聯覺人的回應與先前非常吻合。四年後,科學家再從那1195個詞語中隨意抽出50個作訪問,聯覺人全部答中。仍不滿意?對,負責研究的科學家仍未滿意。實情是,除了重複訪問之外,這兩次相隔四年的研究還做了不少額外且繁複的驗証(又是那六個字:篇幅所限,不贅);最後,科學家還是說了一句:「我信。」(註[4、5])
本文想帶給讀者的是,由於聯覺純是內在主觀的,以科學方法客觀驗証有其根本上的難度,對言者不能盡信的同時,聽者只能以間接方法窺其所思。任何牽涉主觀感覺的研究,與法庭定罪一樣,永遠沒有絕對肯定這回事,只有beyond reasonable doubt。聯覺是不由自主兼且穩定的異常感官,科學家為了証明其存在,創作各種巧妙的實驗,甚至耗費多年心血,這種求真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再次告訴你,我看見64是紅色的,你信唔信?
備註:
[1]Synaesthesia: The prevalence of atypical cross-modal experiences. Julia Simner, Catherine Mulvenna, Noam Sagiv, Elias Tsakanikos, Sarah A Witherby, Christine Fraser, Kirsten Scott, Jamie Ward. Perception (2006) volume 35, pages 1024-1033.
[2]Synaesthesia: An Overview of Contemporary Findings and Controversies. Jamie Ward and Jason B. Mattingley. Cortex (2006) volume 42, pages 129-136.
[3]When coloured sounds taste sweet. Gian Beeli, Michaela Esslen, Lutz Jäncke. Nature (2005) volume 434, page 38.
[4]Lexical-gustatory synaesthesia: linguistic and conceptual factors. Jamie Ward, Julia Simner. Cognition (2003) volume 89, pages 237–261.
[5]Synaesthetic Consistency Spans Decades in a Lexical–Gustatory Synaesthete. Julia Simner, Robert H. Logie. Neurocase (2007) volume 13, pages 358–365.
2009年5月26日 星期二
2009年5月20日 星期三
修理哈勃很「危險」
執筆時,穿梭機阿特蘭蒂斯號上的太空人應該正在忙碌修理哈勃望遠鏡。這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的哈勃維修任務有一特點,就是需要另一架穿梭機奮進號在地面待命,以防太空人萬一遇上什麼「意外」,可以立即升空營救。這不尋常的「舉動」是否代表今次任務特別「危險」?
是,因為目的地是哈勃望遠鏡,而不是國際太空站。
穿梭機升空,大多以國際太空站為目的地,以補給、修建、實驗為目的。任務期間,假如穿梭機遭到任何損壞或故障,而太空人又無法修理,怎麼辦?只有等,在太空站裡面等。美國太空總處現時共有三架穿梭機:發現號、阿特蘭蒂斯號和奮進號,正常情況下,只有最多一架在太空。從前,每次穿梭機升空都有一個附屬的Launch On Need任務,也可說是一個備用但未必執行的拯救行動,以應不時之需;可是,由於計劃和訓練需時,拯救隊最快40天之後方能升空,幸而太空站通常儲存了70至80天的糧食,待援的太空人故無糧斷之慮。今年開始,太空站的儲糧更為充足,只要每次穿梭機按原定日期升空(通常兩次任務相隔不超過四個月),太空人即使被困也可以等待下次救援,Launch On Need任務遂被廢除。可見,美國太空總處對穿梭機因各種原因而未能回航的顧慮非自今日始,關鍵是,糧食多寡決定太空人時日之長短。
今次,穿梭機的目的地是哈勃望遠鏡。不用說,鏡內沒有糧食,倘若穿梭機因某些原因不能回航,太空人只能靠機艙內大約25天的糧食渡日。想到國際太空站?不能,因為望遠鏡跟太空站各有不同的軌道,太空人不能在兩者間穿梭。舊時的Launch On Need也不管用,因為40天後方能起飛,遠水救不了近火。這就是奮進號在發射台候命的原因;如有需要,3天後可以升空,仲快過我買張機票。
奮進號的角色說過了,但哈勃任務比較「危險」的原因不止於此。相信讀者都聽過太空垃圾的問題,大件的包括火箭殘肢和廢棄的人造衛星,小的有爆炸碎片(設計不佳的人造衛星有時會意外爆炸)、機械零件(日久失修的人造衛星可能會有零件脫落)、油漆、碰撞產生的碎片、甚至是太空人不慎丟失的工具(例如一隻手套),各式各樣,想像得到的都有,不要以為體積細小便不用理會,它們的「殺傷力」來自其速度。哈勃望遠鏡離地面約570公里,在這個高度圍繞著地球運行的物體(包括太空垃圾),速度大約每秒8公里;作個對比,子彈也不過是每秒1公里。離地面500至1500公里的範圍是十分「擠擁」的,很多人造衛星以此區域作為其軌道,太空垃圾也特別多,不幸地,哈勃望遠鏡就是位於此區域。國際太空站離地面約350公里,這裡的垃圾較少,被撞的機會也較小。阿特蘭蒂斯號進入哈勃軌道要面對較大「危險」,不言而喻。
相對地面而言,太空始終「地廣星稀」,無論怎樣「擠擁」,真正碰撞的機會應該不大吧。不大是對,但肯定不是零。今年2月便有兩顆人造衛星在西伯利亞上空相撞,是次撞擊增加了太空垃圾的密度,當然也增加了哈勃任務的「危險性」。
美國太空總處對「危險性」必須有具體的量化,才能客觀地評估每個任務是否可行,他們稱這個數字為Loss Of Crew and Vehicle (LOCV) ratio,以1:X表示,X愈小愈危險。這個比例有什麼意義呢?讓我作一簡介。穿梭機回航進入大氣層,為了抵受與空氣摩擦的高溫,機身表面是一層耐熱物料。這層耐熱物料可能被一些微小的太空垃圾撞擊而受損,因此穿梭機回航之前,太空人必須檢查並修復所有「嚴重」瑕疵(什麼叫「嚴重」,什麼是「可以接受」,他們當然又有另一套準則,時間所限,執筆時無暇查閱),假若瑕疵不能修復,穿梭機回航不得,這就是一次LOCV事件。LOCV ratio就是美國太空總處對某次任務會出現LOCV的機會的估計。
影響LOCV ratio的因素非常多,包括任務的長度、太空垃圾的密度、機身的方向、檢查機身的方式等。去年10月的LOCV ratio是1:185,今年2月人造衛星相撞後急降至1:157,後來操作上作些技術性改良,把之推回1:185。可見,這個比例是多麼受外在環境影響,及其「可塑性」有多高。
根據指引,穿梭機任務的LOCV ratio不應大於1:200,話雖如此,美國太空總處是有「酌情權」的。今次哈勃任務,他們有否運用「酌情權」,我卻不能肯定。是次任務正式被批準是在4月30日,此日期前我看到的最後一個LOCV ratio是1:185,但此日期後某些報道卻有1:229之說,185哪個時候被改成229,找不到。以上引用之數字全非第一手資料,若有錯漏,見諒。讀眾中如有知情者,請指教。
除了被動地計算被撞的機率,也可主動地追縱和監測。美國軍方的U.S. Space Surveillance Network其中一項日常工作就是以雷達追縱和監測一些體積較大的太空垃圾,預測可能發生的「太空碰撞」並發出警告,讓有關的人造衛星或航天器有充分距離和時間開動引擎,改變航道以避過碰撞。不過,正如2月的人造衛星相撞事件顯示,監測工作或有百密一疏,又或者衛星負責人慣性地忽略「狼來了」的警告(內情可能遠較複雜,有興趣的讀者應上網查看),當中的技術和人為因素,令這個系統不盡完美。
不說不知,原來哈勃望遠鏡是沒有引擎的,即使預見可能碰撞,也不能迴避,頂多只能調較角度以減低相撞的橫切面,幸好至今安然無恙。今次的維修任務會把其壽命延長四、五年,希望幸運之神繼續眷顧,讓哈勃望遠鏡為科學發展盡最後一分力。
(刊登於2009年5月20日信報副刊)
相關連結:
Assessment of Options for Extending the Life of the Hubble Space Telescope: Final Report
NASASpaceFlight.com:穿梭機新聞
是,因為目的地是哈勃望遠鏡,而不是國際太空站。
穿梭機升空,大多以國際太空站為目的地,以補給、修建、實驗為目的。任務期間,假如穿梭機遭到任何損壞或故障,而太空人又無法修理,怎麼辦?只有等,在太空站裡面等。美國太空總處現時共有三架穿梭機:發現號、阿特蘭蒂斯號和奮進號,正常情況下,只有最多一架在太空。從前,每次穿梭機升空都有一個附屬的Launch On Need任務,也可說是一個備用但未必執行的拯救行動,以應不時之需;可是,由於計劃和訓練需時,拯救隊最快40天之後方能升空,幸而太空站通常儲存了70至80天的糧食,待援的太空人故無糧斷之慮。今年開始,太空站的儲糧更為充足,只要每次穿梭機按原定日期升空(通常兩次任務相隔不超過四個月),太空人即使被困也可以等待下次救援,Launch On Need任務遂被廢除。可見,美國太空總處對穿梭機因各種原因而未能回航的顧慮非自今日始,關鍵是,糧食多寡決定太空人時日之長短。
今次,穿梭機的目的地是哈勃望遠鏡。不用說,鏡內沒有糧食,倘若穿梭機因某些原因不能回航,太空人只能靠機艙內大約25天的糧食渡日。想到國際太空站?不能,因為望遠鏡跟太空站各有不同的軌道,太空人不能在兩者間穿梭。舊時的Launch On Need也不管用,因為40天後方能起飛,遠水救不了近火。這就是奮進號在發射台候命的原因;如有需要,3天後可以升空,仲快過我買張機票。
奮進號的角色說過了,但哈勃任務比較「危險」的原因不止於此。相信讀者都聽過太空垃圾的問題,大件的包括火箭殘肢和廢棄的人造衛星,小的有爆炸碎片(設計不佳的人造衛星有時會意外爆炸)、機械零件(日久失修的人造衛星可能會有零件脫落)、油漆、碰撞產生的碎片、甚至是太空人不慎丟失的工具(例如一隻手套),各式各樣,想像得到的都有,不要以為體積細小便不用理會,它們的「殺傷力」來自其速度。哈勃望遠鏡離地面約570公里,在這個高度圍繞著地球運行的物體(包括太空垃圾),速度大約每秒8公里;作個對比,子彈也不過是每秒1公里。離地面500至1500公里的範圍是十分「擠擁」的,很多人造衛星以此區域作為其軌道,太空垃圾也特別多,不幸地,哈勃望遠鏡就是位於此區域。國際太空站離地面約350公里,這裡的垃圾較少,被撞的機會也較小。阿特蘭蒂斯號進入哈勃軌道要面對較大「危險」,不言而喻。
相對地面而言,太空始終「地廣星稀」,無論怎樣「擠擁」,真正碰撞的機會應該不大吧。不大是對,但肯定不是零。今年2月便有兩顆人造衛星在西伯利亞上空相撞,是次撞擊增加了太空垃圾的密度,當然也增加了哈勃任務的「危險性」。
美國太空總處對「危險性」必須有具體的量化,才能客觀地評估每個任務是否可行,他們稱這個數字為Loss Of Crew and Vehicle (LOCV) ratio,以1:X表示,X愈小愈危險。這個比例有什麼意義呢?讓我作一簡介。穿梭機回航進入大氣層,為了抵受與空氣摩擦的高溫,機身表面是一層耐熱物料。這層耐熱物料可能被一些微小的太空垃圾撞擊而受損,因此穿梭機回航之前,太空人必須檢查並修復所有「嚴重」瑕疵(什麼叫「嚴重」,什麼是「可以接受」,他們當然又有另一套準則,時間所限,執筆時無暇查閱),假若瑕疵不能修復,穿梭機回航不得,這就是一次LOCV事件。LOCV ratio就是美國太空總處對某次任務會出現LOCV的機會的估計。
影響LOCV ratio的因素非常多,包括任務的長度、太空垃圾的密度、機身的方向、檢查機身的方式等。去年10月的LOCV ratio是1:185,今年2月人造衛星相撞後急降至1:157,後來操作上作些技術性改良,把之推回1:185。可見,這個比例是多麼受外在環境影響,及其「可塑性」有多高。
根據指引,穿梭機任務的LOCV ratio不應大於1:200,話雖如此,美國太空總處是有「酌情權」的。今次哈勃任務,他們有否運用「酌情權」,我卻不能肯定。是次任務正式被批準是在4月30日,此日期前我看到的最後一個LOCV ratio是1:185,但此日期後某些報道卻有1:229之說,185哪個時候被改成229,找不到。以上引用之數字全非第一手資料,若有錯漏,見諒。讀眾中如有知情者,請指教。
除了被動地計算被撞的機率,也可主動地追縱和監測。美國軍方的U.S. Space Surveillance Network其中一項日常工作就是以雷達追縱和監測一些體積較大的太空垃圾,預測可能發生的「太空碰撞」並發出警告,讓有關的人造衛星或航天器有充分距離和時間開動引擎,改變航道以避過碰撞。不過,正如2月的人造衛星相撞事件顯示,監測工作或有百密一疏,又或者衛星負責人慣性地忽略「狼來了」的警告(內情可能遠較複雜,有興趣的讀者應上網查看),當中的技術和人為因素,令這個系統不盡完美。
不說不知,原來哈勃望遠鏡是沒有引擎的,即使預見可能碰撞,也不能迴避,頂多只能調較角度以減低相撞的橫切面,幸好至今安然無恙。今次的維修任務會把其壽命延長四、五年,希望幸運之神繼續眷顧,讓哈勃望遠鏡為科學發展盡最後一分力。
(刊登於2009年5月20日信報副刊)
相關連結:
Assessment of Options for Extending the Life of the Hubble Space Telescope: Final Report
NASASpaceFlight.com:穿梭機新聞
2009年5月14日 星期四
疾病跨物種
找到疾病跨種傳染的例子。注意,這裡不是所有例子,只是一些例子,notable absence包括1918大流感後人類把H1N1傳給豬,和最近人類把metapneumovirus傳給黑猩猩。
資料來源:Emerging pathogens: the epidemiology and evolution of species jumps. Mark E.J. Woolhouse, Daniel T. Haydon, Rustom Antia. 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 Volume 20, Issue 5, May 2005. [Abstract][PDF]
| Pathogen | Original host | New host | Year reported |
| Transmissibl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ies | |||
| BSE/vCJD | Cattle | Humans | 1996 |
| Viruses | |||
| Rinderpest | Eurasian cattle | African ruminants | Late 1800s |
| Myxoma virus | Brush rabbit/Brazilian rabbit | European rabbit | 1950s |
| Ebola virus | Unknown | Humans | 1977 |
| FPLV/CPV | Cats | Dogs | 1978 |
| SIV/HIV-1 | Primates | Humans | 1983 |
| SIV/HIV-2 | Primates | Humans | 1986 |
| Canine/Phocine distemper virus | Canids | Seals | 1988 |
| Hendra virus | Bats | Horses and humans | 1994 |
| Australian bat lyssavirus | Bats | Humans | 1996 |
| H5N1 influenza A | Chickens | Humans | 1997 |
| Nipah virus | Bats | Pigs and humans | 1999 |
| SARS coronavirus | Palm civets | Humans | 2003 |
| Monkeypox virus | Prairie dogs | Humans | 2003* |
| Bacteria | |||
| Escherichia coli O157:H7 | Cattle | Humans | 1982 |
| Borrelia burgdorferi | Deer | Humans | 1982 |
| Fungi | |||
| Phytophthora infestans | Andean potato | Cultivated potato | 1840s |
| Cryphonectria parasitica | Japanese chestnut | American chesnut | Late 1800s |
* Monkeypox was first reported in humans in 1970, but infections acquired from prairie dogs were not seen until 2003.
資料來源:Emerging pathogens: the epidemiology and evolution of species jumps. Mark E.J. Woolhouse, Daniel T. Haydon, Rustom Antia. 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 Volume 20, Issue 5, May 2005. [Abstract][PDF]
2009年5月13日 星期三
流感.豬場.雞場.ball場
上星期引述美國疾控中心病毒學專家Ruben Donis的說法,新型豬流感的全部基因皆來自豬隻流感,而非人鳥豬混合體;至於地理源頭,上回語焉不詳,現借Eurosurveillance於4月30日的一個報告作些補充。此報告認同所有八段基因皆源自豬隻流感,其中兩段來自歐亞大陸,餘下六段來自北美洲。這與Donis的說法(兩段亞洲,一段不明,五段沒提及)並無抵觸,因為歐亞豬隻交往頻繁,其身上的病毒故可視為一家。至此,科學家對基因來源總算有個共識,儘管兩地病毒如何「洗牌」仍屬未知。
流感病毒變種之速度和靈活,是其對特效藥產生抗藥性和我們對其不能產生永久免疫力的底因,加上以H乜N乜命名和同時可以在人、鳥、豬之間流傳的多樣性,不單容易令人「眼花撩亂」,想替其解畫也不知從何說起。今天,就讓我以一個比喻,把甲型流感病毒具體地描繪出來。(精簡起見,以下所說的「流感」是指甲型流感,不包括乙型和丙型。)
病毒是一團蛋白;流感病毒由11種蛋白組成,這些蛋白與細胞的互動決定病毒對寄主的影響。基因是製造蛋白的「指令」,流感病毒擁有8段基因。換句話說,它用8段基因給自己製造11種蛋白。想像,流感病毒是一支由8位球員擔當11個崗位的球隊,球隊表現由各個崗位的表現決定,崗位由球員擔任,故球員乃是球隊之基本。崗位多過球員,所以某些球員必須兼顧多於一個崗位(即某些基因負責製造多於一種蛋白)。球隊中,最重要的兩個崗位叫H和N。精簡起見,我會稱「擔當H崗位的球員」為「H球員」;「N球員」意義類同。
球隊以H球員和N球員的「風格」命名。每個球員有自己的風格,例如力量型、技術型或工兵型等。所有H球員可被劃分為16種風格(H1-H16),N球員可被劃分為9種風格(N1-N9)。 H1N1,意即以第1種風格踢H崗位配合第1種風格踢N崗位的球隊。無論讀者是不是球迷,也應該知道整隊的踢法不可能以四個字完全表達。首先,風格類別只是一些「大類」,兩位球員即使屬同一大風格,也必然有自己的小風格;其次,不要忘記一隊有8人,只以其中兩人命名,無異於以兩位球星判斷整隊表現。H乜N乜,除了作為名稱之外無甚意義,兩個病毒縱使名稱相同,並不代表它們對某類藥物呈相同反應,也不代表某疫苗對它們同時有效。兩個病毒名稱相同,只代表它們擁有同一(大)類的H和N蛋白,除此之外,別無他意。
流感球隊能夠在三種場地上作賽:人、鳥、豬的身體。有想像力的讀者可以視之為草地場、石屎場和爛地場,我就選擇較直接的比喻方式:豬體是「豬場」,鳥體是「雞場」,人體可以叫「人場」,但與「人牆」同音且同是球壇術語,因此我比較喜歡「ball場」(雖然與「波長」同音,唯兩者通常在不同情況下出現,不易混淆)。每支流感球隊都有其擅長的場地,這特徵不易改變,在豬場踢慣波的球隊傾向繼續留在豬場,在ball場打滾慣的也喜歡繼續留連ball場,像H5N1間中由雞場走到ball場作賽,或ball場上突然出現了一支全由豬場球員組成的H1N1球隊,不常見。「踩場」,是大件事。
球隊的名稱與擅長的場地沒有必然關係。有踢慣豬場的H1N1,也有蒲慣ball場的H1N1,單憑名稱不能確定其「主場」。(這裡是說「踢慣」,像新型豬流感般從豬場「踩」來ball場,是另一回事。)話雖如此,某些方面仍是有跡可尋。例如,近年在人與人之間流傳的大都是H1N1和H3N2,豬隻之間流傳的大都是H1N1、H1N2、H3N1和H3N2,禽鳥最為兼收並畜,體內可容納H和N的多個組合。看來,雞場確是龍蛇混雜之地。
流感球隊打的是淘汰賽,是沒完沒了的淘汰賽,獎品不是獎杯,而是「複製」的機會。正常而言,複製出來的每位球員都是完美翻版,與先前一模一樣,可是複製過程並不完美,翻版時有錯漏,新球員的風格與「先輩」可能稍有出入,打球既是群體運動,牽一髮可以動全身,新球隊運作如何,預測不準,落場方見真章。如果新球隊是「虎父犬兒」,不免會被淘汰;反之,假若「青出於藍」,便可繼續複製,流芳百世。這個變異、競爭、敗者被淘汰、勝者再變異的循環,就是進化論「適者生存」的精髓。可是,優劣沒有絕對標準,除了自身條件,還有客觀因素,在家鄉打不贏嗎,到異鄉也許可以創一番事業。病毒沒有人的自由意志,但因著寄主的際遇,偶然會被帶到一塊新場地,球隊能否在此立足,卻要看其造化。大家熟悉的H5N1,雖然間中踩場成功,可幸未能人傳人。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是禽鳥的H1N1跑到人類身上來,並且發展出人傳人的本領。踩場成功,還能夠人傳人,非常非常大件事。
複製的變異是漸進的,「洗牌」的變異是突然的。所謂「洗牌」,即是球隊之間交換球員,當兩個流感病毒在同一個細胞內相遇,它們的基因便可能混在一起。今次新型豬流感球隊,是由兩位歐亞大陸的豬場球員和六位北美豬場球員組成。1957年的亞洲流感是H2N2,是人、鳥混種,其中包括三位雞場球員和五位ball場球員。1968年的香港流感是H3N2,也是人、鳥混種,包括兩位雞場球員和六位ball場球員。
以上提及的1918、1957、1968全球流感疫潮(pandemic),估計死亡人數(根據維基百科)依次為四千萬、一百至一百五十萬、七十五至一百萬;世衛對pandemic的定義取決於其傳播的廣泛程度,即使死亡率低,只要足夠多的人染病,醫療系統的負荷和死亡人數也會很高。個人而言,我比較關心死亡率,1918流感的死亡率是2.5%,後二者和一般季節性流感相差不遠,都少於0.5%;H5N1的死亡率是奇高的超過50%;至於新型豬流感,根據世衛5月11日的最新消息,有4694宗確診病例,其中包括53宗死亡,死亡率為1.1%。
看來,純粹鳥傳人的流感病毒(1918和H5N1)遠比「洗牌」而成的流感病毒(1957、1968和新型豬流感)可怕,並非什麼科學論據,只是個人觀察。
想深一層,也不知是病毒可怕,還是人類可悲。我們自詡為萬物之靈,想不到從另一角度看,只是被病毒球隊任意蹂躪的ball場。
(刊登於2009年5月13日信報副刊)
相關連結:
除了1918流感死亡率為公認的2.5%,其他各次的準確死亡率言人人殊,讀者可從這些連結得到一些rough idea……
Virology blog swine flu update (7 May 2009)
WHO Europe: Health Evidence Network
Time Online: Swine flu Q&A
Evidence-based public health policy and practice: Finding the real case-fatality rate of H5N1 avian influenza
WHO: Epidemiology of human H5N1 cases
超好的流感背景資料,用心讀,可以學到很多。
Influenza Report 2006
Avian influenza: assessing the pandemic threat
流感病毒變種之速度和靈活,是其對特效藥產生抗藥性和我們對其不能產生永久免疫力的底因,加上以H乜N乜命名和同時可以在人、鳥、豬之間流傳的多樣性,不單容易令人「眼花撩亂」,想替其解畫也不知從何說起。今天,就讓我以一個比喻,把甲型流感病毒具體地描繪出來。(精簡起見,以下所說的「流感」是指甲型流感,不包括乙型和丙型。)
病毒是一團蛋白;流感病毒由11種蛋白組成,這些蛋白與細胞的互動決定病毒對寄主的影響。基因是製造蛋白的「指令」,流感病毒擁有8段基因。換句話說,它用8段基因給自己製造11種蛋白。想像,流感病毒是一支由8位球員擔當11個崗位的球隊,球隊表現由各個崗位的表現決定,崗位由球員擔任,故球員乃是球隊之基本。崗位多過球員,所以某些球員必須兼顧多於一個崗位(即某些基因負責製造多於一種蛋白)。球隊中,最重要的兩個崗位叫H和N。精簡起見,我會稱「擔當H崗位的球員」為「H球員」;「N球員」意義類同。
球隊以H球員和N球員的「風格」命名。每個球員有自己的風格,例如力量型、技術型或工兵型等。所有H球員可被劃分為16種風格(H1-H16),N球員可被劃分為9種風格(N1-N9)。 H1N1,意即以第1種風格踢H崗位配合第1種風格踢N崗位的球隊。無論讀者是不是球迷,也應該知道整隊的踢法不可能以四個字完全表達。首先,風格類別只是一些「大類」,兩位球員即使屬同一大風格,也必然有自己的小風格;其次,不要忘記一隊有8人,只以其中兩人命名,無異於以兩位球星判斷整隊表現。H乜N乜,除了作為名稱之外無甚意義,兩個病毒縱使名稱相同,並不代表它們對某類藥物呈相同反應,也不代表某疫苗對它們同時有效。兩個病毒名稱相同,只代表它們擁有同一(大)類的H和N蛋白,除此之外,別無他意。
流感球隊能夠在三種場地上作賽:人、鳥、豬的身體。有想像力的讀者可以視之為草地場、石屎場和爛地場,我就選擇較直接的比喻方式:豬體是「豬場」,鳥體是「雞場」,人體可以叫「人場」,但與「人牆」同音且同是球壇術語,因此我比較喜歡「ball場」(雖然與「波長」同音,唯兩者通常在不同情況下出現,不易混淆)。每支流感球隊都有其擅長的場地,這特徵不易改變,在豬場踢慣波的球隊傾向繼續留在豬場,在ball場打滾慣的也喜歡繼續留連ball場,像H5N1間中由雞場走到ball場作賽,或ball場上突然出現了一支全由豬場球員組成的H1N1球隊,不常見。「踩場」,是大件事。
球隊的名稱與擅長的場地沒有必然關係。有踢慣豬場的H1N1,也有蒲慣ball場的H1N1,單憑名稱不能確定其「主場」。(這裡是說「踢慣」,像新型豬流感般從豬場「踩」來ball場,是另一回事。)話雖如此,某些方面仍是有跡可尋。例如,近年在人與人之間流傳的大都是H1N1和H3N2,豬隻之間流傳的大都是H1N1、H1N2、H3N1和H3N2,禽鳥最為兼收並畜,體內可容納H和N的多個組合。看來,雞場確是龍蛇混雜之地。
流感球隊打的是淘汰賽,是沒完沒了的淘汰賽,獎品不是獎杯,而是「複製」的機會。正常而言,複製出來的每位球員都是完美翻版,與先前一模一樣,可是複製過程並不完美,翻版時有錯漏,新球員的風格與「先輩」可能稍有出入,打球既是群體運動,牽一髮可以動全身,新球隊運作如何,預測不準,落場方見真章。如果新球隊是「虎父犬兒」,不免會被淘汰;反之,假若「青出於藍」,便可繼續複製,流芳百世。這個變異、競爭、敗者被淘汰、勝者再變異的循環,就是進化論「適者生存」的精髓。可是,優劣沒有絕對標準,除了自身條件,還有客觀因素,在家鄉打不贏嗎,到異鄉也許可以創一番事業。病毒沒有人的自由意志,但因著寄主的際遇,偶然會被帶到一塊新場地,球隊能否在此立足,卻要看其造化。大家熟悉的H5N1,雖然間中踩場成功,可幸未能人傳人。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是禽鳥的H1N1跑到人類身上來,並且發展出人傳人的本領。踩場成功,還能夠人傳人,非常非常大件事。
複製的變異是漸進的,「洗牌」的變異是突然的。所謂「洗牌」,即是球隊之間交換球員,當兩個流感病毒在同一個細胞內相遇,它們的基因便可能混在一起。今次新型豬流感球隊,是由兩位歐亞大陸的豬場球員和六位北美豬場球員組成。1957年的亞洲流感是H2N2,是人、鳥混種,其中包括三位雞場球員和五位ball場球員。1968年的香港流感是H3N2,也是人、鳥混種,包括兩位雞場球員和六位ball場球員。
以上提及的1918、1957、1968全球流感疫潮(pandemic),估計死亡人數(根據維基百科)依次為四千萬、一百至一百五十萬、七十五至一百萬;世衛對pandemic的定義取決於其傳播的廣泛程度,即使死亡率低,只要足夠多的人染病,醫療系統的負荷和死亡人數也會很高。個人而言,我比較關心死亡率,1918流感的死亡率是2.5%,後二者和一般季節性流感相差不遠,都少於0.5%;H5N1的死亡率是奇高的超過50%;至於新型豬流感,根據世衛5月11日的最新消息,有4694宗確診病例,其中包括53宗死亡,死亡率為1.1%。
看來,純粹鳥傳人的流感病毒(1918和H5N1)遠比「洗牌」而成的流感病毒(1957、1968和新型豬流感)可怕,並非什麼科學論據,只是個人觀察。
想深一層,也不知是病毒可怕,還是人類可悲。我們自詡為萬物之靈,想不到從另一角度看,只是被病毒球隊任意蹂躪的ball場。
(刊登於2009年5月13日信報副刊)
相關連結:
除了1918流感死亡率為公認的2.5%,其他各次的準確死亡率言人人殊,讀者可從這些連結得到一些rough idea……
Virology blog swine flu update (7 May 2009)
WHO Europe: Health Evidence Network
Time Online: Swine flu Q&A
Evidence-based public health policy and practice: Finding the real case-fatality rate of H5N1 avian influenza
WHO: Epidemiology of human H5N1 cases
超好的流感背景資料,用心讀,可以學到很多。
Influenza Report 2006
Avian influenza: assessing the pandemic threat
2009年5月12日 星期二
1918 > 2009 ≈ 1957
專家對新型豬流感的傳染性和死亡率作了最新估計,應該沒有1918年西班牙流感那麼嚴重,可能與1957年亞洲流感相約。不過,由於疫情仍在進行中,資料未全,這只是一個非常暫時性的估計。
2009年5月8日 星期五
豬流感的基因構成
Eurosurveillance,4月30日,The origin of the recent swine influenza A(H1N1) virus infecting humans,有他們對豬流感來源之解讀:8段基因其中兩段來自歐亞大陸,六段來自北美。H基因的來源,他們比Ruben Donis來得肯定一點,總的來說兩者說法大致吻合。這篇比較易明,有興趣的讀者大可一讀。
不update死亡人數了,很悶。那「101宗」疑似死亡好像已經在傳媒消聲匿跡,只見兩位數字的確診死亡,減少混淆和誤解,誠屬好事。
不update死亡人數了,很悶。那「101宗」疑似死亡好像已經在傳媒消聲匿跡,只見兩位數字的確診死亡,減少混淆和誤解,誠屬好事。
2009年5月7日 星期四
2009年5月6日 星期三
豬流感的3個事實
(本文刊於2009年5月6日信報)
先叫豬流感,現稱H1N1甲型流感,鍾南山說應該叫北美流感,歐洲稱其為新流感(novel flu)。叫什麼名稱不重要,最重要是不可得罪豬農。說出口的原因永遠是名稱不能「誤導」,意即要「反映事實」,用最精簡的詞彙反映最多的事實。實情卻是,短短幾個字根本載不下事實的全部。
事實一:這病毒的基因全部來自豬隻流感,而不是坊間所說的人、鳥、豬混合體。
我不是行內人,說得這麼肯定,非有一個權威的資料來源不可。美國疾控中心病毒學專家Ruben Donis(銜頭chief of the molecular virology and vaccines branch)於4月29日接受了ScienceInsider(科學期刊Science旗下的科學新聞網站)的訪問,回應了記者對今次病毒源頭的誤解。 Donis的說話十分technical,沒有足夠的background很難明白,讓我為大家解解畫。
H1N1,其實是指病毒表面的兩種蛋白:第1類H蛋白和第1類N蛋白。現時為止我們共發現了16類H蛋白(H1-H16)和9類N蛋白(N1-N9)。不要太在意H和N究竟是什麼,反正只是些化學名詞的代號,讀者只需知道,病毒其實是一團蛋白,這些蛋白與我們身體細胞的互動決定病毒對我們的影響。讀者也要認清基因和蛋白的關係:基因是生產蛋白的「指令」,病毒變種,意即其基因變異,造出來的蛋白與先前會有少許不同,對身體的影響或增加或減少,不能事前預測,只有試過才知道。所有甲型流感病毒都是由11種蛋白(包括H和N,還有兩種叫M1和M2,統稱M,下面會再提及)和8段基因組成,即是8段基因包含了11項製造蛋白的「指令」。
借用Donis的比喻,流感病毒像一支有8個球員的球隊,球隊之間可以任意互換球員。人、鳥、豬的病毒之所以能夠混合,皆因流感球隊可以互換基因的靈活性,坊間俗稱「洗牌」。關於這次豬流感,可以肯定的有兩點:其一,所有基因都是來自豬隻病毒;其二,N和M蛋白的基因來自亞洲。H蛋白的基因和所有已知的品種都不吻合,來源地不明。其餘五段基因,文中沒有提及,我也不便猜測。無論如何,最不尋常之處是忽然有兩段亞洲基因跟六段非亞洲基因混在一起。至於這個「洗牌」最先在哪個地方發生,在哪種動物(可以是人)身上發生,不知道。精明的讀者可以能會問,如果所有基因都是來自豬隻,這個「洗牌」不是應該在豬隻身上發生嗎?可以,但未必。一個人可以從兩個地方的豬隻同時感染兩個品種的豬流感(這個當然是指在豬隻之間流傳的「舊式」豬流感,不是本文主題可以人傳人的「新型」豬流感),然後那兩個品種再在人身上混種。分清楚,感染和生病是兩回事,病毒進入身體未必會引致生病的徵狀,又或者只是小病,看過醫生算了也不出奇。重點是,即使混種成功也未必立刻致命和可以人傳人,再經過多少次變異才達致今日的「境界」,無人知道。
病毒來自墨西哥的豬,只是想當然的假設。事實上,數天前加拿大艾伯塔省的豬隻受感染(5月4日信報頭版),才是全球首次在豬隻身上發現這病毒。重覆一次,所有基因來自豬隻流感,但「洗牌」何時何地何種動物身上發生,不知道。
為何有「人鳥豬混合體」的說法呢?Donis說,這要回到1998年,當時有一種H3N2流感在豬隻之間肆虐,此病毒是人鳥豬混合體,感染力非常強,傳播極之廣泛,自此疫潮之後,豬隻身上出現的大多是此病毒的「後裔」,所以今次豬流感的基因也有其「影子」,「人鳥豬混合體」的說法遂不徑而走。實情是,原本那混合體及其「後裔」已經在豬隻身上「落地生根」自成一系達十年之久,完全適應了宿主的生理環境,以合乎常理的看法,怎也不應再稱為「人鳥豬混合體」,而是不折不扣的豬流感病毒。Donis以自己原是阿根廷人,卻自1980年己移居美國作比喻,在公眾場合,你應該稱他為美國人還是阿根廷人呢?答案當然是前者。我家族幾十代之前可能是北方人,但今日我只會稱自己為廣東人;追本溯源都要有個限度。
知道這個事實,這種新型流感又應該怎樣稱呼呢?我認為叫「豬源頭H1N1甲型流感」(Swine-origin Influenza A(H1N1))最貼切,也是學術和醫學界常見的一個叫法。公眾不會接受,因為太累贅;香港現在普遍以「甲型H1N1流感」謂之。可是,精簡是有代價的,有時會引起混淆甚至誤會,以下就是一個十分好的例子。
事實二:截至4月28日止,豬源頭H1N1甲型流感並未對特敏福呈抗藥性。
5月4日信報頭版: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表示,現存H1病毒當中,百分之九十八對特敏福呈抗藥性。
矛盾?非也。讓我替後者加三個字: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表示,現存H1〔人流感]病毒當中,百分之九十八對特敏福呈抗藥性。明未?
其實H1N1病毒一直在人與人之間流傳,這些活在人體已久的品種經已發展出對特敏福的抗藥性;新型豬流感同屬H1N1類型,對特敏福卻呈不同的反應。權威資料來源?當然有。美國疾控中心「Antiviral Drugs and H1N1 Flu (Swine Flu)」網頁原文節錄:Laboratory testing on these swine influenza A (H1N1) viruses so far indicate that they are susceptible (sensitive) to oseltamivir and zanamivir. Oseltamivir是特敏福的學名,zanamivir市面上叫Relenza(中文名我不肯定)。以上說的laboratory testing早在4月28日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的快電(dispatch)中提及,13個豬流感樣本全對以上兩種藥物「不」呈抗藥性。
「現存H1病毒當中,百分之九十八對特敏福呈抗藥性」是事實,但絕對不是事實的全部。將來怎樣,無人知道,但至少4月28日為止,特敏福對新型豬流感仍然有效。(交稿前再作查詢,沒有找到更近期的試驗結果。)
事實三:截至5月5日香港時間晚上8時止,墨西哥的確診死亡個案從未超過26宗。香港傳媒廣泛引用的「101宗死亡」,是疑似死亡個案。
網上找不到墨西哥的第一手官方數據,唯有根據網上新聞的搜尋結果,差不多所有官方訊息都是由衛生部長Jose Angel Cordova發放。4月29日之前,確診死亡數目一直維持在20,港聞聽到過百的,其實是疑似死亡個案,即「好像」因流感而死,但不肯定是否因新型豬流感而死。4月29日,來了第一次調整,確診死亡數目由20減至7(看報導一、二)。5月2日,再來一次調整,這次是疑似死亡,由176減至101(看報導一、二),當時的確診死亡已增至16。這次調整也是比較「惹人注目」的一次,有些市民更以為墨西哥當局一下子把數字從176調低至16,惹來很多不必要的諷刺和挖苦。此後,看來墨西哥當局學乖了,公佈的死亡數字只有一個,就是確診死亡,以免引起混淆,這與世衛的做法吻合。
流感爆發初期,墨西哥當局的訊息發放固然混亂,但我認為香港傳媒也難辭其咎,既然訊息混亂,又為何說得如此言之鑿鑿?兩位數的確診死亡,永遠被三位數的疑似數字蓋過。某些傳媒在那三位數字旁邊更沒有放上「疑似」字眼,又是那一句,唔可以話你錯,但這不是事實的全部。
墨西哥的消息不可信?世衛消息可信了吧。自4月24日開始,世衛已經每日更新世界各地的確診和疑似個案數目。墨西哥的確診死亡,由4月27日的7宗,遞增至5月5日的25宗。世衛對個案核實非常嚴謹,用以發放消息的句子和字眼也非常清晰,確診死亡數字未有被傳媒廣泛採用,想必是其未達三位數字之原故。(交稿前再作查詢,世衛的數字仍是25,墨西哥當局的最新數字是26。)
本文用的資訊,大多已有一週之齡,在疫情迅速發展的今天,或者略嫌過時,只是資料搜集和整理著實費時,見諒。如果我能夠在云云資訊中爬梳出一些被忽略的細節,釋除一些困惑和誤解,這篇文章也沒有白寫了。
後記:本文見報的版本,分段小標題為報館所加。通常我對小標題無甚意見,但本篇小標題之一「並非來自墨西哥豬隻」,不確。文中提及「病毒來自墨西哥的豬,只是想當然的假設」,重點是「不知道」病毒來自何地何種動物,說它來自墨西哥的豬,不確;說它「並非」來自墨西哥的豬,也不確。小事一樁,我不介懷,只是公眾對豬流感已經夠多誤解,不想再加多一項。
先叫豬流感,現稱H1N1甲型流感,鍾南山說應該叫北美流感,歐洲稱其為新流感(novel flu)。叫什麼名稱不重要,最重要是不可得罪豬農。說出口的原因永遠是名稱不能「誤導」,意即要「反映事實」,用最精簡的詞彙反映最多的事實。實情卻是,短短幾個字根本載不下事實的全部。
事實一:這病毒的基因全部來自豬隻流感,而不是坊間所說的人、鳥、豬混合體。
我不是行內人,說得這麼肯定,非有一個權威的資料來源不可。美國疾控中心病毒學專家Ruben Donis(銜頭chief of the molecular virology and vaccines branch)於4月29日接受了ScienceInsider(科學期刊Science旗下的科學新聞網站)的訪問,回應了記者對今次病毒源頭的誤解。 Donis的說話十分technical,沒有足夠的background很難明白,讓我為大家解解畫。
H1N1,其實是指病毒表面的兩種蛋白:第1類H蛋白和第1類N蛋白。現時為止我們共發現了16類H蛋白(H1-H16)和9類N蛋白(N1-N9)。不要太在意H和N究竟是什麼,反正只是些化學名詞的代號,讀者只需知道,病毒其實是一團蛋白,這些蛋白與我們身體細胞的互動決定病毒對我們的影響。讀者也要認清基因和蛋白的關係:基因是生產蛋白的「指令」,病毒變種,意即其基因變異,造出來的蛋白與先前會有少許不同,對身體的影響或增加或減少,不能事前預測,只有試過才知道。所有甲型流感病毒都是由11種蛋白(包括H和N,還有兩種叫M1和M2,統稱M,下面會再提及)和8段基因組成,即是8段基因包含了11項製造蛋白的「指令」。
借用Donis的比喻,流感病毒像一支有8個球員的球隊,球隊之間可以任意互換球員。人、鳥、豬的病毒之所以能夠混合,皆因流感球隊可以互換基因的靈活性,坊間俗稱「洗牌」。關於這次豬流感,可以肯定的有兩點:其一,所有基因都是來自豬隻病毒;其二,N和M蛋白的基因來自亞洲。H蛋白的基因和所有已知的品種都不吻合,來源地不明。其餘五段基因,文中沒有提及,我也不便猜測。無論如何,最不尋常之處是忽然有兩段亞洲基因跟六段非亞洲基因混在一起。至於這個「洗牌」最先在哪個地方發生,在哪種動物(可以是人)身上發生,不知道。精明的讀者可以能會問,如果所有基因都是來自豬隻,這個「洗牌」不是應該在豬隻身上發生嗎?可以,但未必。一個人可以從兩個地方的豬隻同時感染兩個品種的豬流感(這個當然是指在豬隻之間流傳的「舊式」豬流感,不是本文主題可以人傳人的「新型」豬流感),然後那兩個品種再在人身上混種。分清楚,感染和生病是兩回事,病毒進入身體未必會引致生病的徵狀,又或者只是小病,看過醫生算了也不出奇。重點是,即使混種成功也未必立刻致命和可以人傳人,再經過多少次變異才達致今日的「境界」,無人知道。
病毒來自墨西哥的豬,只是想當然的假設。事實上,數天前加拿大艾伯塔省的豬隻受感染(5月4日信報頭版),才是全球首次在豬隻身上發現這病毒。重覆一次,所有基因來自豬隻流感,但「洗牌」何時何地何種動物身上發生,不知道。
為何有「人鳥豬混合體」的說法呢?Donis說,這要回到1998年,當時有一種H3N2流感在豬隻之間肆虐,此病毒是人鳥豬混合體,感染力非常強,傳播極之廣泛,自此疫潮之後,豬隻身上出現的大多是此病毒的「後裔」,所以今次豬流感的基因也有其「影子」,「人鳥豬混合體」的說法遂不徑而走。實情是,原本那混合體及其「後裔」已經在豬隻身上「落地生根」自成一系達十年之久,完全適應了宿主的生理環境,以合乎常理的看法,怎也不應再稱為「人鳥豬混合體」,而是不折不扣的豬流感病毒。Donis以自己原是阿根廷人,卻自1980年己移居美國作比喻,在公眾場合,你應該稱他為美國人還是阿根廷人呢?答案當然是前者。我家族幾十代之前可能是北方人,但今日我只會稱自己為廣東人;追本溯源都要有個限度。
知道這個事實,這種新型流感又應該怎樣稱呼呢?我認為叫「豬源頭H1N1甲型流感」(Swine-origin Influenza A(H1N1))最貼切,也是學術和醫學界常見的一個叫法。公眾不會接受,因為太累贅;香港現在普遍以「甲型H1N1流感」謂之。可是,精簡是有代價的,有時會引起混淆甚至誤會,以下就是一個十分好的例子。
事實二:截至4月28日止,豬源頭H1N1甲型流感並未對特敏福呈抗藥性。
5月4日信報頭版: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表示,現存H1病毒當中,百分之九十八對特敏福呈抗藥性。
矛盾?非也。讓我替後者加三個字: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表示,現存H1〔人流感]病毒當中,百分之九十八對特敏福呈抗藥性。明未?
其實H1N1病毒一直在人與人之間流傳,這些活在人體已久的品種經已發展出對特敏福的抗藥性;新型豬流感同屬H1N1類型,對特敏福卻呈不同的反應。權威資料來源?當然有。美國疾控中心「Antiviral Drugs and H1N1 Flu (Swine Flu)」網頁原文節錄:Laboratory testing on these swine influenza A (H1N1) viruses so far indicate that they are susceptible (sensitive) to oseltamivir and zanamivir. Oseltamivir是特敏福的學名,zanamivir市面上叫Relenza(中文名我不肯定)。以上說的laboratory testing早在4月28日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的快電(dispatch)中提及,13個豬流感樣本全對以上兩種藥物「不」呈抗藥性。
「現存H1病毒當中,百分之九十八對特敏福呈抗藥性」是事實,但絕對不是事實的全部。將來怎樣,無人知道,但至少4月28日為止,特敏福對新型豬流感仍然有效。(交稿前再作查詢,沒有找到更近期的試驗結果。)
事實三:截至5月5日香港時間晚上8時止,墨西哥的確診死亡個案從未超過26宗。香港傳媒廣泛引用的「101宗死亡」,是疑似死亡個案。
網上找不到墨西哥的第一手官方數據,唯有根據網上新聞的搜尋結果,差不多所有官方訊息都是由衛生部長Jose Angel Cordova發放。4月29日之前,確診死亡數目一直維持在20,港聞聽到過百的,其實是疑似死亡個案,即「好像」因流感而死,但不肯定是否因新型豬流感而死。4月29日,來了第一次調整,確診死亡數目由20減至7(看報導一、二)。5月2日,再來一次調整,這次是疑似死亡,由176減至101(看報導一、二),當時的確診死亡已增至16。這次調整也是比較「惹人注目」的一次,有些市民更以為墨西哥當局一下子把數字從176調低至16,惹來很多不必要的諷刺和挖苦。此後,看來墨西哥當局學乖了,公佈的死亡數字只有一個,就是確診死亡,以免引起混淆,這與世衛的做法吻合。
流感爆發初期,墨西哥當局的訊息發放固然混亂,但我認為香港傳媒也難辭其咎,既然訊息混亂,又為何說得如此言之鑿鑿?兩位數的確診死亡,永遠被三位數的疑似數字蓋過。某些傳媒在那三位數字旁邊更沒有放上「疑似」字眼,又是那一句,唔可以話你錯,但這不是事實的全部。
墨西哥的消息不可信?世衛消息可信了吧。自4月24日開始,世衛已經每日更新世界各地的確診和疑似個案數目。墨西哥的確診死亡,由4月27日的7宗,遞增至5月5日的25宗。世衛對個案核實非常嚴謹,用以發放消息的句子和字眼也非常清晰,確診死亡數字未有被傳媒廣泛採用,想必是其未達三位數字之原故。(交稿前再作查詢,世衛的數字仍是25,墨西哥當局的最新數字是26。)
本文用的資訊,大多已有一週之齡,在疫情迅速發展的今天,或者略嫌過時,只是資料搜集和整理著實費時,見諒。如果我能夠在云云資訊中爬梳出一些被忽略的細節,釋除一些困惑和誤解,這篇文章也沒有白寫了。
後記:本文見報的版本,分段小標題為報館所加。通常我對小標題無甚意見,但本篇小標題之一「並非來自墨西哥豬隻」,不確。文中提及「病毒來自墨西哥的豬,只是想當然的假設」,重點是「不知道」病毒來自何地何種動物,說它來自墨西哥的豬,不確;說它「並非」來自墨西哥的豬,也不確。小事一樁,我不介懷,只是公眾對豬流感已經夠多誤解,不想再加多一項。
2009年5月1日 星期五
食左fing頭丸的鸚鵡
鸚鵡的舞蹈天份不是今日方被發現,只是最近才有生物學家以科學方法証實鸚鵡的確是會限隨音樂的節拍搖擺。看看這兩個video,佢地真係可以跳得好「型」!
下面呢隻我肯定佢食o左fing頭丸……
資料來源:
Hey birds! So you think you can dance??
下面呢隻我肯定佢食o左fing頭丸……
資料來源:
Hey birds! So you think you can dance??
訂閱:
意見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