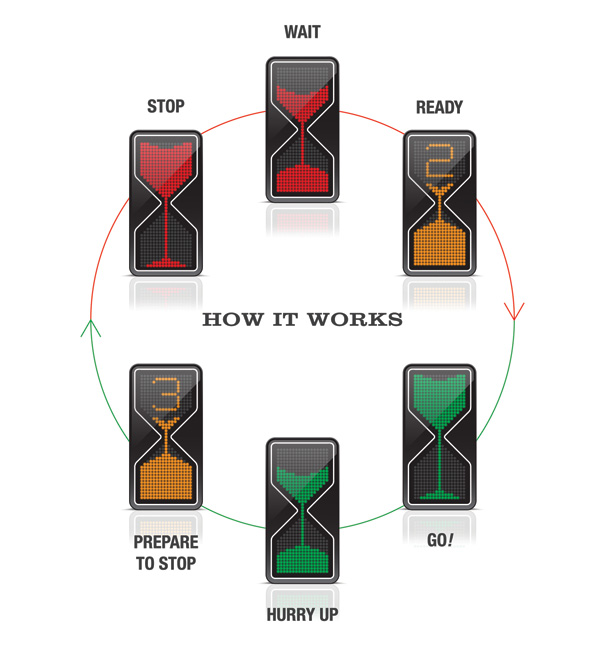記者:「年尾製作世界大事回顧的最佳材料。沒有它們,我早已失業。」
無國界醫生:「又是我出動的時候……well,山火未必,但其餘四件,我都會去。」
受虐者:「每件事都曾經發生在我身上,慘劇每晚都會發生。你以為阿富汗才有戰爭嗎?我家每天都在打仗。你怕朝鮮局勢一觸即發?爸爸每秒都一觸即發。死不是最恐怖,活在恐懼之中才是最恐怖。」
天災人禍,新聞有刊載的,通常都是「大件事」。然而,在泛光燈照不到的幽暗角落,有着千千萬萬不值一提的小事件、小悲劇。我們知道汶川大地震,卻不知道每年有超過一百萬次小地震;知道歷年華南水災,卻無暇兼顧成千上萬的小泛濫;記得八仙嶺大火,香港每年上千宗山火你知道嗎?兩次世界大戰眾所周知,而忘卻了無數內戰和衝突;九一一歷歷在目,昨天發生多少次恐怖襲擊你又知不知道?
大災難必上頭條,受害人亦得到各方憐憫和幫助;日常社會天天發生諸如黑幫械鬥、謀殺、強姦、縱火、虐待等小規模悲劇,我們又知道多少?每一件「大事」給大肆報導,有多少件「小事」被忽略及遺忘?「大事」和「小事」發生的頻率有沒有規律呢?
英國人 Lewis Richardson 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已經思考類似問題,他想,戰爭、暴動、謀殺骨子裡都是人與人的衝突,是人類侵略性的體現,雖然背景迥異,其中有否一些隱藏規律呢?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了二千多萬人,美國內戰「只」死了六十多萬,謀殺受害者由一至數個不等,此等懸殊的「規模」,有何規律可言?Richardson 收集了 1820 至 1945 年所知戰爭的死亡人數,並以英國和威爾斯的謀殺案例估算全球謀殺比率(一次謀殺可視為一次超小型戰爭),發現戰事規模與頻率成反比,傷亡愈慘重愈是罕見,死傷愈輕愈是常見;假如這是唯一發現,不說也罷,但當他把數據繪成圖表,以死亡人數為橫軸,出現頻率為縱軸(兩軸皆為對數),圖中的點竟由左上至右下成一直線!
 在對數圖形成一條傾向右下方的直線(如右圖),符合這形態的算式泛稱「power law」,換言之,人類衝突顯示 power law 的形態。事實上,地震、洪水、山火、恐怖襲擊也符合 power law,其規模和頻率繪成對數圖,也會成一條傾向右下方的直線。有「power」之稱,因為數式的主要部分為某數的負次方,「次方」的英文是「power」,故名。
在對數圖形成一條傾向右下方的直線(如右圖),符合這形態的算式泛稱「power law」,換言之,人類衝突顯示 power law 的形態。事實上,地震、洪水、山火、恐怖襲擊也符合 power law,其規模和頻率繪成對數圖,也會成一條傾向右下方的直線。有「power」之稱,因為數式的主要部分為某數的負次方,「次方」的英文是「power」,故名。Power law 這名字,大家可能覺得陌生,「黑天鵝現象」應該聽過吧。「黑天鵝」指一些理論上極為罕見、但實際上偶有出現的大震盪(例如股市大瀉),為什麼理論與現實不符呢?研究社會現象的學者,通常假設數據「正常分佈」(normally distributed),「正常分佈」的數字不會離平均值太遠,走向極端的機率極低,這顯然與事實不符。相反,power law 容許極端情況發生(儘管可能性較低),「黑天鵝」的出現顯得較為合理,用來解釋現象比較恰當。在「正常分佈」的框架下,「黑天鵝」是一個謎;在 power law 的框架下,「黑天鵝」早在意料之內。
與 Richardson 同一年代,另一名叫 George Zipf 的學者發現又一有趣現象。把美國城市根據人口排名,其人口比例恰好是排名的比例,例如,第二位城市的人口是第一位的 1/2,第三位人口是第二位的 2/3,如此類推,第一百位人口是第九十九位的 99/100。這是 Zipf's law,用在英語詞彙也可以,「the」是最常用的詞語,「of」次之,後者出現的頻率恰好是前者的 1/2。
Zipf's law 是 power law 的一種。Power law 不僅形容天災人禍,很多社會現象也可以,說 power law 無處不在,不算誇張。
80/20 法則,大家應該聽過。用 20% 努力拿到 80 分,餘下的 20 分卻往往需要 80% 努力,付出愈多,所得遞減。這法則也體現在財富分佈,最富有的兩成人士控制社會上八成財富,另一端看,最窮困的八成人口只佔所有財富的兩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這是 80/20 法則的另一解讀。會考成績又如何?兩成學生拿去八成分數?兩成學校拿去八成「A」?有沒有這樣懸殊,研究過才知。樓市呢?兩成房屋佔去八成市值?比例會不會隨樓市興衰而改變?又一有趣課題。
80/20 法則由意大利人 Vilfredo Pareto 在上世紀初所創,據他所說,財富分佈也跟隨 power law,80/20 法則實是 power law 的另一體現。
Power law 無處不在,遠至無法預測的大地震,近至自食其果的金融海嘯,小至事不關己的謀殺案,大至影響深遠的世界大戰,看似風馬牛不相及,有的天然,有的人為,為什麼竟然隱藏着同一秩序?學者未有答案。對於個別現象,他們能夠提出一些頗具解釋力的模型,但暫時還沒有一套「集大成」的理論涵蓋所有 power law 現象。
某次與親戚飲茶,談到我替信報撰文,一人問:「信報?邊個睇呀?」另一人衝口而出:「最有錢嗰啲人咪睇囉!」真有洞見!的確,信報讀者多是幸運的一群,位處或接近 power law 的頂端,享受着 power law 給幸運兒帶來的好處。對於貧苦老百姓而言,「power law」可能另有所指;他們心目中,「power law」所代表的,可能是「power breeds power」,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又或者如英文諺語所言「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2010 年 12 月 22 日 信報副刊)
後記:線上遊戲魔獸世界,最活躍的 11% 玩家佔去過半的遊戲時間,與 80/20 法則如出一轍。最沉迷一星期玩 149 小時,平均每天 21.3 小時。
學術參考:
Juan Camilo Bohorquez, Sean Gourley, Alexander R. Dixon, Michael Spagat, Neil F. Johnson (2009), “Common Ecology Quantifies Human Insurgency,” Nature 462, 911-914. doi:10.1038/nature08631
M. E. J. Newman (2005), “Power laws, Pareto Distributions and Zipf's Law,” Contemporary Physics 46, 323-351. doi:10.1080/00107510500052444
Lars-Erik Cederman (2003), “Modeling the Size of Wars: From Billiard Balls to Sandpil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7, 135-150.
Lewis F. Richardson (1948), “Variation of the Frequency of Fatal Quarrels With Magnitud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43, 523-546.